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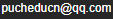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读完了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很好的一本薄薄的书。
人的孤独感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克服的办法一是创造,主动去改造自然,实现自我和外部世界直接的联通;另一个就是爱,分享自己的生命力,实现自我和人群之间的联通。无论是创造还是爱,都是主动性的行为;所以弗洛姆提倡“创造性的人格”。
通俗地说,爱是给予而不是理解。爱确实是内心强大的表现。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说,感情是弱者的感情,但是,过于脆弱的相互依靠的感情可能也无法真正健康而长久。我赞成说,一个懂得并且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独处,而不求助于各种他者(包括人和物)的支持――才有着真正的去爱人的力量。真正的爱里,就应能够同时成就自己和他人。无论是一味索取的爱,还是按照自己的臆想一味给予并且认为对方需要的爱,都是不健康的。
弗洛姆也超多探讨了现代社会是否有利于爱的培养的问题,他认为,西方社会导致了爱的溃散;其主要论据在于,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带来了现代人与自身、与其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了。我赞同,在工业大革命之后,“物”在人类生活中享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崇拜;但是我不敢肯定,在现代社会之前,爱是普遍的,而现代社会的到来,带来了爱的溃散。可能确实现代对于人之间关系的抨击很多,从文学到哲学的各个方面,但是更加可能是由于人的信仰变化――从崇拜爱与美到崇拜物而贬低人――而造成的。我们甚至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对自己的心灵更加敏感或者麻木。所谓协作精神和相互体谅对于相处的作用,我想不只是现代会这么要求――人和人是不同的,相处之间摩擦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同理心和让步就是必要的润滑剂,而非某个社会形态强加在于人身上的,只但是大众媒体会不会这样坦诚。
让步假设说,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爱的溃散,这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美德标准带来了这样的状况来概括。如果爱――博爱、母爱、性爱,能够给人带来愉悦,那么人就不会轻易放手它们,不会因为社会崇尚协作精神,就贸然提议说,我们放下相互之间的爱,用协作好处上的共生来替代吧。――人应对鱼和熊掌的第一反应,不会是,两者我该放下哪一个,而首先会是,我能不能同时占用两者。另外,如果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起意在于学会爱,获得幸福感,那么笼统而轻巧地把职责推于社会形态是一种既不负职责又无济于事的行为――我们大能够把时间花在一部电影一桶爆米花,而不是严肃的思考上。
但是,我们确实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或者说工业化的进程,确实改变了人的很多习惯、特征;这样特征和习惯的改变可能最终改变了社会里爱的现状。
确实,现代社会里更多幸福感来源于消费――或者说,人的幸福感向来部分来自于消费,而在工业化之前,消费部分占有份额受到了消费品总量的限制,无法大幅扩张;而工业化带来了这样的可能性,于是人自然地转向这部分更加容易增长的幸福来源,从而构成了大众逐利的场面;而这样的状况有可能造成了大家对于精神层面替代性的忽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许国际贸易里“福利恶化型”增长的状况会出现。
同时,现代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习性。弗洛姆在“爱的实践”里所提到了几种爱的基本要求:“自律”、“专注”、“耐心”、“极大的热情”(discipline,concentration,patience,passion)。但是现代社会的物质消费约束集确实不利于这些美德的培养,这些美德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远不如一两千年前。我们能够说,人性的的进化是缓慢的,远远慢于意识形态的演化,更加慢于生产力的提升――尤其是在生产力经历了指数甚至更快的增长之后。不可能指望植根于人性的意识形态迅速地能够适应生产力的提升,而同时持续了当初的种种坚韧不摧(或者至少在没有外界冲击状况下,表面的坚韧不摧)。因此,爱成为一种需要学习、时时注意的潜力――培养这样潜力之始,就是从努力靠近弗洛姆所提出的几项要求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