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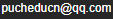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中国传统织绣纹样源出古老的中华文化,与中国传统陶瓷纹样、铜器纹样、玉雕纹样、建筑纹样等异曲同工,折射了中华文明的别样风采。作者认为,纹样孕育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富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及民俗学意义,意境深远。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之于政治,乃社会人等身份品级不可僭越的礼制规定:万千纹样上下亲疏有别,维系着政治和伦理秩序;纹样之于经济,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技术水准乃至生活水平:自远古时代茹毛饮血的渔猎,及至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耕稼,纹样的题材、风格、配色、造型莫不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的变迁;纹样之于宗教,集中表现了华夏先民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凝聚了人们对于自然神力的虔诚信仰;而龙图腾兼具恐鳄、惊蛇、爱豚、赞鹿、羡鹰之精神寄托,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其纹样成为至尊之代表;崇尚生命繁衍的生殖图腾则以抓鸡娃娃、鲤鱼闹莲、凤戏牡丹、交颈鸳鸯、榴开百子、蝶恋花等谐趣无穷、浮想联翩的借代纹样广为流传……
作者舒展了哲学思维,他写到,中国传统织绣纹样设计汲中华古代文明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之精华,在造型、布局及配色方面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法则,营造出富于辩证变化且又和谐始终、回味无穷的绝妙意境,堪称中华文化风格的杰出体现。在造型上,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形体构成无不依阴阳变化之律,或刚柔相济,如该书所举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之龙凤虎纹绣衣;或动静结合,如民间常见之飞蝶花卉纹、明清帝王龙袍及百官蟒袍下脚之海水疆牙纹;或曲直相间,如敦煌莫高窟出土之北魏忍冬团巢龟背纹刺绣花边、明清常见之冰梅纹;或屈伸交感,如唐代之卷草纹;或具象和抽象互现,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至唐墓出土之方格兽纹锦、隋唐之连珠纹锦、宋之八答晕和明之天华锦……其有机结合巧夺天工,浑然一体而又毫不做作。在布局上,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排列充满了虚与实、聚与散、大与小、疏与密的对比和变化,貌似对立的组合取得了生动的和谐。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配色同样不同凡响,明暗、冷暖、纯度和色相对比强烈,协调有度,在一张一弛间充满变化,予人以一种美学享受。中华文明崇尚的“天地人和”,在中国传统织绣纹样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作者的研究功力在对于中国传统织绣纹样发展史的把握中反映出来。1929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出土的戈形兵器上,有明显的织物印纹;1950年安阳武官村殷墓出土的铜戈上,有丝绢印痕;其他墓葬出土的铜爵、铜觚、铜钺等器物上,也屡见丝织物印痕,甚至连织物上的回纹、条纹和雷纹,都清晰可辨。近30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的丝织品文物出土颇多,尤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大宗,这些丝织品色彩丰富,纹样精美,组织复杂。汉代以后,提花技术不断进步。唐代的提花技术更为精湛,丝织物花纹硕大丰满,色彩富丽。常见的绫锦花样有盘龙、对凤、拱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芝草、双胜以及吉祥文字等,史籍中有不少记载,实物也有大量发现。宋元以后,有关织造工艺的文献记载更为丰富,元代薛景石的《梓人遗制》、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代杨屾风广义》等著作不仅对织机的构造、织工的操作有详尽叙述,而且有附图,为人们了解古代织造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明清时期丝织物传世颇多,织绣纹样进一步发展变化,完整的织机也有传存,在南京、苏州及杭州等地,至今还保留着花镂机提花的传统工艺。刺绣与织造不同,刺绣在已经织出的布帛上另作加工,用绣针牵引彩线,按设计好的图样刺扎出花纹。刺绣纹样同样源远流长,绚丽斑斓。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织绣纹样的发展,更见其历史的穿透力、文化的凝聚力和艺术的感染力。 共2页,当前第1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