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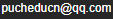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谁也不知道巴金撰写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信是老朋友潘际写的。潘际供职于《大公报》,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
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她们的墓碑竟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
巴金的《谈〈望乡〉》在香港《大公报》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于是潘际就再次约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当时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他感到自己应该写一部同类的作品。当潘际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名为《随想录》。
巴金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巴金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自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
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投稿。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信上写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潘际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潘际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
看了潘际的回信,巴金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对潘际叹息说:“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