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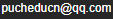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忘不了上届六年级一个叫文浩的小男孩讲给我听的故事。
他爷爷奶奶是养鱼的,常年住在距离村子五六里路的荒野里,守着十一二亩的水面,鱼塘四周是农田环绕,南面开了一个口子,由农家船进进出出,口子用网拦着,船来放下,船走拉起,整整三道坝,防止鱼趁着船进出的当儿往外逃窜,当然这网口子还能将外面大河里的活水引进来。二老养鱼最怕夏天,浮萍、水花生一股脑涌到网口子附近,连接东西两岸的拦网被挤压,紧绷绷的,像一张拉开的弓,他爷爷奶奶在烈日炎炎中不停地将水花生拖走,浮萍捞起搁在河堤上。夏天更怕鱼塘反水,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大量缺氧会导致与大批死亡,二老没日没夜守着,像看小孩一般细致。河里还要撒硫酸铜,河沿撒石灰,河中央的增氧泵没日没夜鼓着浪像喷泉。在荒野过活,小屋是简易移动板房,蓝顶白墙,里面有煤气灶、纱门纱窗,通了有线电视自来水,还是在一个夏日,文浩的父亲在二老毫无知晓的情况下给装了空调。其实在夏天晚间,野地里四面来风,凉爽得很。只是白天晒得像蒸笼,家里人生怕二老在荒僻处有个闪失。
小文浩轮到双休日以及假期就喜欢到爷爷奶奶那儿去钓钓鱼,活杀以后红烧、清蒸、昂刺鱼汆汤加点醋,虎头鲨汆汤则浓白,奶奶变着花样哄他撩他,有时把一寸左右的鰟鮍、虎头鲨、罗汉鱼在面糊里滚一遭,放在锅里油炸,香酥可口,有时手头活儿忙,清理好盐腌了放在太阳下晒干,搁上葱蒜姜浇点油炖着吃。文浩吃腻了,池塘上还有活杀的鸡鸭,爷爷捡来的野鸡蛋,路上一棍砸死的蛇。文浩去那儿不仅仅是吃,他喜欢那里的春花夏蛙秋虫,冬天爷爷奶奶一般也就回村了。他喜欢在野田里能看见一丝不挂的天空,喜欢听芦苇在风中沙沙歌吟。荒野里各种树在疯长,鸟儿隐匿在茂密的枝叶间,他喜欢看嵌在枝桠间的鸟巢,真神奇,就是一团泥巴和横七竖八的树枝,任你风吹雨打,它自岿然不动。他更喜欢爷爷宽厚的肩膀,奶奶温情的手掌,祖孙仨围着小桌吃饭时爷爷喝两口小酒看奶奶的眼睛清亮,像泉。这一切描绘了文浩童年的缤纷记忆。
一年春时,爷爷因无由的病痛走了,爸爸妈妈把奶奶从鱼塘边的小屋夺了回来,鱼塘以及所有设施转包给他人。中元节祭祀,文浩放筷子时发现北、东、西各两只白底蓝花的碗,唯独南面是一只碗,后来奶奶眼睛朝桌子上看了一眼,将那碗边的筷子从右边移到左边,爷爷是左撇子。
是爷爷的碗,文浩多看了几眼,一道斜斜的裂缝自上而下,破裂处钉了个铁扒子,能看见油泥抹实裂缝与钉眼的痕迹。很是纳闷,可这神圣的时刻也不好问什么,磕头时口中念叨着“爷爷、各位祖宗回家吃饭拿钱。”他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那破碗,孤零零的一只,左撇子的爷爷应该在安详坐着吧。
祭祀过后,奶奶把那破碗反复汰洗,再用手巾擦干,最后用一条崭新的蓝头巾仔细包好放到柜子里,凄然,庄重。
文浩看看奶奶再瞅瞅父亲。
父亲告诉他:“这是奶奶从鱼塘带回的唯一家什。”
“这碗你奶奶已经保存了三十几年了。”
父亲顿了一下。“你爷爷年轻时喜欢打麻将,输了回来就发脾气。有次跟奶奶吵,生气时将碗摔了,就这只。奶奶含着泪将这碗收起来到城里找箍碗匠花了五只碗的费用修补好。她故意那这碗盛饭给你爷爷吃,用过一次,你爷爷就把这碗放进碗柜里。”
“后来他们还吵架,最多就是摔摔笤帚枕头还有不锈钢茶杯。再后来,心境也就平和了。”父亲说:“修好的碗终究有条缝,看得刺眼,硌得心痛。这道理你奶奶懂,爷爷明白了。”
文浩讲故事在桂子飘香的秋,这年寒假过后她妈妈来报名,我问起孩子的父亲,“早早去郑州打工了,哪边活计催得紧。”她羞赧地笑了,恰似嗅着青梅的女子,教室里隐约多了一丝古老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