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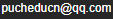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1
皖水上游的怒潮冲过乌石堰奔泻而下,硬生生在那古皖平原上,撕开一条八百米宽的河道。尔后,一路左冲右突,纵横驰骋,直至炫耀干净了最后一丝武勇,方逗留在沙帽洲喘了口气,于斜阳残影里,欲语还休般遁入长江。
乌石堰下游十里处的坝脚下,倚了座相公庙。古庙安卧于田畴之畔,暮鼓晨钟,静观红尘变迁。历代以来,家乡皆有关于相公菩萨的传说。而在近代,故事的主人公,竟然是爷……
2
那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家乡梅城也迎来了第一次解放。乡亲们打着小红旗,将解放军拥进城,正准备斗地主分田地哩,谁料国军突然又杀了个回马枪。乡亲们没奈何,只好掉头去欢迎回城的国军。欢迎的锣鼓尚未平息,刘邓大军又赶跑了国军。爷说那几年里,乡亲们来来去去就做了两件事,欢迎解放军进城,和欢迎国军进城。
挨到民国三十八年春,解放军摧枯拉朽,卷地而来。眼瞅石磨也挡不住城门了,国民党县长只得领着溃兵,往黄泥港一带寻活路,抢粮拉夫自成了跑路前的压轴戏。这天,爷正在田里忙活,乱兵们围了上来,二话不说,拿绳绑了便走。奶哭喊着撵去,大兵们一顿枪托,打得奶顺原路又爬了回来。
爷和一众民夫抬着县长姨太太,在那雨点般鞭梢的催促下,夹在末路的队伍里,逃向黄泥港。天黑后,邻居胡爷悄声鼓动爷:“咱哥儿俩逃命去吧!”爷自是想逃,但见四下皆是背着枪的乱兵,迟疑着没敢答应。
夜半,胡爷起身小解,刚钻进树林,便撒腿狂奔起来。溃兵们吃了败仗,正无处发泄,闻声追了上去,一阵乱枪,爆豆般炸响了夜空。爷胆怯地闭紧了眼,心里直打着鼓。不一时,乱兵骂咧咧地回来了。爷不安地睁开眼,看时,胡爷已被扔在众人面前,那身上的血窟窿,筛眼儿也似,汩汩淌着血。胡爷血糊满面,虽说断了气,两眼却似灯笼般瞪着,爷只瞥了眼,浑身已抖成一团。
四月中旬,解放军如从天降。逃命比面子更重要,县长的姨太太撇了轿子民夫,裹在乱军中,火急地逃往乡下。解放军雄赳赳地撵了上来,问民夫们:“老乡,干革命吗?”爷心里挂念着奶,哪愿参军?解放军也不勉强,只说匪兵还没消灭干净,路上可能不太平。于是,爷一众暂留在了黄泥港。
黄泥港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在城南五十里处。因这儿进可攻、退可守的地势,不仅梅城的国军残兵逃来了,安庆的大刀会迫于形势,也逃在附近。猫吃鱼,狗吃屎,臭味相投的两股残匪很快勾搭上了。又打探得刘邓大军已经渡江,留守空虚,觉得咸鱼翻身的机会到了,双方一合计,决定干票大买卖,攻占共产党黄泥港区政府。
当日,大刀会会众焚香祈祷,筑坛拜将,小喽啰们祭出杏黄旗,将那附近村寨插了个遍。是夜,月黑风高,那二千多名喝足了朱砂水的会徒,红布裹头,白布扎腰,左手芭蕉扇,右手大刀片,擂鼓鸣锣,口念咒语:“刀枪不入,杀不尽,打不进,观音老母来保命。”乌泱泱,潮水般朝黄泥港区政府蜂拥而来。国军残兵皆被打怕了,惊弓之鸟般,猫着腰,紧随其后。
此时,区政府仅剩一班人马驻守,但武器精良。大刀会在乡下击鼓传兵,折腾了一天,排场很足,闹出的动静更大,班长早得到消息,埋伏好了人马,只等兵匪上门。
再说爷一众人等,见多日没有动静,遂收拾了行李,准备次日回家。正说笑间,班长来了,将晚上要打仗的事说了,大伙儿面面相觑,尽皆失色。班长让大家躲进后屋,莫要声张。众人怕被流弹伤着,皆趴在地上,嘴里哆哆嗦嗦,皇天后土地祈求平安。
眼见那冲进区政府大院里的会众,虽高举着大刀片,却都是些穿着粗布烂衫的农民。解放军不忍向众人射击,只是对天鸣枪。会徒们受了愚弄,不明就里,误以为刀枪不入的神功见效了,越发像打了鸡血般亢奋,如潮似浪,向前冲砍。
无奈之下,解放军搂开了火,前排会徒望风而倒,后排会众仍痴迷不悟,鼓噪呐喊着冲锋。眨眼间,会徒们涌到近前,开枪已来不及了,解放军只好架起钢炮,打出了几发炮弹,一时间,硝烟弥漫,一片鬼哭狼嚎声中,却见胳膊腿满天乱飞。这时,被裹挟的会徒才明白,那刀枪不入的神功,皆是骗人的把戏,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怎挡得了快枪炮弹?后面的人发一声喊,乌合之众,国军残兵,尽作鸟兽散。
深夜,爷和众人探头探脑,从后屋走了出来,帮解放军清理战场。区政府院里院外,高高燃起了灯烛火把,只见那残肢断臂,飞溅了一地。一个小战士喊住了爷,两人抬起一具趴在地上的尸体,翻过身,借火光一看,却见这会徒被手榴弹炸开了胸腹,肝脏肠子,一半留在体内,一半流出体外,那一摊摊鲜血,直染红了地面。
爷是个安分老实的庄稼汉,平日里侍弄的多是土地谷种,何曾见过这等残酷的战争场面?一阵阴风吹来,爷只觉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直冲脑门儿,舌根当时便硬了,哪还说得出半句话来?爷浑身筛糠,壮着心胆,将惨死的会徒抬出院门,码到墙角下。
爷擦了把额头的冷汗,心神犹自不安,才走回院里,迎面又有个战士招呼道:“老乡,搭把手呀!”爷怕得要命,却还是咬牙走了去。见地上躺着个国军残兵,脑壳被弹片削去大半,那黏糊糊的脑浆,溢出裂开的颅骨,和着鲜血,一片红一片白,淌得满地皆是。这还不算,那人的左眼珠炸得飞了出来,仅剩一丝血肉相连着,悬在空洞洞的眼眶下面。右眼珠死鱼般,胀得圆鼓鼓的,凸出眼眶,正深仇大恨地瞪着爷。爷吓得魂不附体,大叫一声,眼前一黑,人也软绵绵瘫了下去……
爷这一觉,直睡到次日晌午。班长安慰道:“老乡,昨晚让你受了惊吓,搁这儿歇几天吧!”三天后,爷仍是打不起精神来,但思家心切,哪还呆得下去?便随解放军拉粮的马车,到了县城,又深一脚浅一脚,腾云驾雾般从县城回了乌石堰。
3
爷被溃兵抓走后,奶整日泪眼倚门,张望着门前的大路,怔怔出神。爷奶皆生于乱世,他们的往事,风雨沧桑。
乌石堰是座拦水堤坝,在梅城西北二十里处。皖水势如蛟龙,自乌石堰呼啸而过。因而,这段河道也被称为了蛟河。当地有三姓大户家族,沿河世居。
曾祖父是位书生,继承先人遗训,在乌石堰读书耕田。蛟河中游,偌大的村庄,聚居着郭氏族人。民国五年,曾祖父娶了位郭家姑娘为妻,这姑娘便是曾祖母。第二年春上,曾祖母有了身孕,夫妻二人,欢喜不尽。
可世事无常,清明那天,曾祖父穿件长衫,撑把黄伞,回头朝曾祖母微微一笑,转身走进了淅沥的小雨中。每年清明,曾祖父定会过一趟乌石堰,去对岸的山上祭扫祖坟。谁知这次,曾祖父一去未归。数天后,乌石堰下游的河道里,却浮出了曾祖父的遗体。
曾祖父莫名其妙死在蛟河,这下可苦了曾祖母。好在族众仁义,婶娘妯娌们日夜不离,陪侍在曾祖母身边,曾祖母方熬过了那场凄风苦雨。年冬,爷来到世间的那声哀啼,惊得窗外雨雪纷纷。世道动荡,满目凄凉,孤儿寡母,怎的活命?
九个月后,曾祖母寻件长褂,裁得短了,将爷兜在怀里,改嫁到了蛟河下游的汪老屋。那汪家的曾祖父,也生在半耕半读的家族,他的父亲,德隆望重,乃是汪氏族长。
爷是曾祖父的遗腹子,随曾祖母在汪家长至二十来岁,又返回乌石堰,继承曾祖父的香火。曾祖父年纪轻轻,突然亡故了,哪有家产留下?爷回来时,老屋早坍塌了,蒙族里关照,权在祠堂边上的两间角屋里暂歇。
安身的地儿有了,娶媳妇却成了天大的难题。爷熬到快三十岁时,媒婆刘婶在收了担谷子后,终于答应为爷寻门亲事。爷身材高大,相亲那天,爷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外套马褂,那气宇轩昂的样子,让奶一见倾心,二话没说,当即应允了这门婚事。
新婚之夜,奶傻眼了。爷心虚地瘫坐在土坯床上,脑袋低得直插进了裤裆。爷嗫嚅交代了借来礼帽、长衫、马褂骗亲的经过。爷嘟囔完了,却没迎来那场预料中的暴风骤雨。奶在爷磕磕巴巴的坦白过程中,长叹一声,认命了。
婚后,奶井然有序地打理起爷家的生活,过了几年,日子才渐渐红火起来。好不容易苦尽甘来,爷却又无端被乱兵抓走,生死不明,奶虽有主见,却也一下陷入了迷茫的沼泽。
可爷竟毫发无伤地回来了,这让奶大喜过望,奶觉得日子又有盼头了。但仅过了一天,奶却再次品尝到了恐慌的滋味。爷虽回来了,却像是魔怔了,整日语无伦次,只是絮叨说他怎么被抓到黄泥港,怎么给人抬轿子,怎么遍地淌着血,怎么死人码得像柴垛子……间或,还指着空中,胡乱呵斥。后来,爷不说不闹了,只扯着鼾声,没日没夜地酣睡。
奶心急如焚,请来了许郎中。许郎中医术精湛,十里八村无人不晓。平常人家孩子,偶有个头痛脑热,只须许郎中赐几颗药丸,包管次日连蹦带跳,鲜活如初。纵遇沉疴宿疾,许郎中几剂汤药,一套银针下来,病人也立马容光焕发了。
许郎中穿着长衫,背着药箱,迈着方步,进了爷家,来不及喝茶客套,直接来到床前。许郎中张开五指,在爷眼前晃了晃,爷没丁点儿反应。又伸手把住爷的脉门,侧着身子,微闭双目,沉思许久,才对奶说:“我尽力试试吧!”许郎中打开药箱,从药箱里拿出个长方形檀木盒,又打开木盒,却见里面从粗到细,从长到短,依次排列着十八根银针。针灸疗法是许家的祖传绝技,许郎中的父亲,曾用针灸的方法,治好了邻县一位失语多年的哑巴,在家乡名噪一时。
许郎中取出四根细长的银针,分别插在爷双眉间的印堂穴、左右太阳穴和人中穴,然后手捏针尾,深入浅出,轻搓慢捻。奶立在一旁,屏声静气,眼巴巴看着许郎中。一炷香后,许郎中轻轻拔出四根银针,用鹿皮细细擦拭干净,依次放回盒里。再看爷被银针刺过的穴位,慢慢渗出黑色血丝来。许郎中用纤细的中指沾了血丝,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然后皱紧了眉,摇摇头,站起身来,用袖口擦擦额头密集的汗珠,背起药箱,一脸歉意地对奶说:“他嫂子,人已不行了,早点儿准备后事吧!”奶听了,宛如五雷轰顶,惊得呆了。许郎中不安地搓着双手,叹惜着,出门走了。
奶正扑在爷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却听屋外有人连声喊道:“大嫂、大嫂!”奶强忍悲痛,抬眼一看,却是爷的二弟进屋来了。当初,曾祖母改嫁到汪家后,又给爷生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二爷爷说,曾祖母听说爷回来了,放心不下,派他前来打探一下消息。奶哽咽着,便将许郎中的话,告诉了二爷爷。二爷爷虽然年轻,但在曾祖母悉心调教下,却很机智沉稳。二爷爷认真看了昏睡的爷,并没惊慌失措,却宽慰奶说:“大哥身上,并无致命的创伤,许郎中医术高明,却说无能为力,这其中必有缘由。”又说,“大嫂只管守护着大哥,我要再去找许郎中问个明白。”奶这才恍然大悟过来。
却说许郎中从爷家回到药堂,放下药箱,还未来得及脱下长衫,二爷爷随后便跟了进来。二爷爷一声不吭,只紧紧盯着许郎中看。许郎中被盯得心里发毛,挠了挠头,说:“唉!医生只能治病,却不能治命呀!你大哥的病,我真没法子了。”二爷爷不卑不亢,说:“咱这蛟河地界,还从未听说有许先生治不了的病。”许郎中一时语塞,想了想,招呼二爷爷坐下,说:“中医认为,每个人的元神,皆由魂魄凝聚而成,俗称‘三魂七魄’。人一死,魂魄便自行消散。你大哥的状况,依我看,应是惊吓过度,魂魄早已离身了。”
二爷爷闻言,心有不甘,问:“我大哥才三十来岁,家里一切全靠他主张。先生能不能施回春妙手,再想想法子?”许郎中沉吟半晌,方说:“这已不是医生的汤药针炙所能挽救的了。”说完,许郎中瞟了瞟二爷爷。二爷爷是极聪明伶俐的,见许郎中瞅得这般意味深长,心中一动,试探着问道:“先生指的是相公菩萨?”许郎中不置可否,微微一笑。二爷爷赶紧起身告辞,临行,向许郎中深鞠一躬:“多谢先生点拨。”
4
原来那时,家乡一带兵荒马乱,三灾六难的邪乎事儿不少,平常人家遇到疑难,实在不能决断时,便去庙里祈求相公菩萨的保佑。
二爷爷不敢耽搁,沿着蛟河,匆匆赶回家中,把爷的情况以及许郎中的话,俱对父母说了。曾祖母听罢,双手紧紧揪住前襟,心都碎了。汪家的曾祖父此时已继承了族长之位,见曾祖母如此着急,安慰道:“我马上去相公庙,找寺里的老和尚商量个对策。”相公庙就在汪老屋村后的坝脚下,前后两进,规模不大,但环境清幽,殿宇森严。曾祖父气喘吁吁赶到庙里,老和尚问明情由,引了曾祖父到菩萨面前,说:“替孩子祷个告吧!”
告子是一副陀螺状的木头模具,但从中剖为两半,面朝天的称为公告,面朝地的称为母告。曾祖父跪在菩萨面前,虔诚祈祷:“我儿全忠,昨为兵匪所掳,饱受惊吓,魂魄离身,命在旦夕。弟子诚意,恭请菩萨发慈悲心肠,为全忠追回魂魄。弟子沐菩萨大恩,没齿不忘。”祷毕,老和尚松开手,只听“叭”一声响,两只告子双双坠地,打了几个滚儿,正好一公一母躺在地上。老和尚大喜,对曾祖父说:“圣告。菩萨同意了,快回去准备吧!”曾祖父磕头不止。
曾祖父一溜烟儿赶回家,拿出封信,交给二爷爷,嘱咐道:“你套上马车,即刻去三祖寺,务必请来八位高僧,天黑前赶回庙里。”又吩咐三爷爷,“蛟河渡口,已备下竹排,你马上过河,去平原村白云观,找到丁道长,烦他带七位徒弟,日落前赶到你大哥家。”二爷爷、三爷爷各自领命,匆忙而去。曾祖父又发动族众,分头准备当晚为爷喊魂事宜,曾祖母也托人分别去娘家族里和乌石堰,让各做准备。
曾祖父安排已毕,又宽慰了一番曾祖母,匆匆返回相公庙。过了一个多时辰,三爷爷方喘着气,进了庙门。曾祖父尚未开口,三爷爷抢着说:“丁道长领一众高徒,已上路了。”曾祖父欣慰地点点头。正说话间,族里的妇女们,挑着香油柴禾和米面菜蔬来了。曾祖父交代妇女们去斋堂准备斋饭。妇女们身后,走来精挑细选的八位壮实小伙,这八人肩上,抬了顶“大花轿”。轿子用八张太师椅拼绑而成,上面铺着锦缎彩帛。花轿甫一落地,众人围拢上来,连声称奇,庙门前顿时热闹起来。
看看红日平西,二爷爷还没消息,曾祖父焦躁起来。老和尚正劝慰间,忽听坝头上马匹嘶鸣,曾祖父大喜过望:“来了来了。”二爷爷引着八位手执锡杖、肩背包袱的法师,从坝上依次走了下来。老和尚急步趋前,和师弟们合掌行礼。众人进了相公庙,分宾主而坐,寒暄了一阵儿,便有管事的妇女说斋饭好了。八位法师、抬轿青年、曾祖父、老和尚、二爷爷、三爷爷、一众族人,分成六桌,安静用斋。斋饭结束,天也黑了,相公庙大殿的两壁厢,高高燃起了香烛油灯,照得亮如白昼。五月间的皖西南,草木葱茏,春意正浓。入夜后,天空中忽降下了一层薄雾,倚着蛟河大坝的这座古庙,在朦胧夜雾的笼罩下,像幅飘在浮云上的剪影般,分外沉寂肃穆。
曾祖父和老和尚相互对视了一眼,点点头说:“时辰已到,开始吧!”老和尚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今晚要恭请相公菩萨大驾,为全忠喊魂,诸位一切听从族长指挥,不得高声喧哗,交头接耳。不得随意走动,失惊打怪。”八位高僧,分成两列,一齐打开随身包袱取出僧帽戴在头上,又取出绛红色袈裟披在身上。众僧席地而坐,再取出木鱼铜磬摆在身前,左手不停数拨佛珠,右手敲响木鱼铜磬,嘴里唱起经文,诵的却是《金刚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在皖西南相公庙为爷喊魂的那个夜里,八位高僧朗朗的诵经声传出庙门,飘向村野。众人屏气凝神,虔诚静听。约摸过了半个时辰,诵经声激越高亢起来,木鱼铜磬敲得密如急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众人只觉头皮阵阵发紧,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佛说是经已,广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僧众的诵经声,随着最后一记铜磬颤鸣,瞬间平静下来。与此同时,曾祖父一声暴喝:“恭请相公菩萨起驾。”八位精壮小伙早已准备停当,同声回应:“恭请菩萨起驾。”声如炸雷,直震殿宇。八位青年一齐跪倒,在菩萨面前“嘭嘭”磕头,然后起身,小心翼翼抬起菩萨像身,轻轻安放在庙门前的花轿上。
曾祖父嘱咐二爷爷:“你引领菩萨,径往全忠家去。丁道长已在那边接应,我和师父们只在庙里,静候佳音。”二爷爷左手举着火把,右手挑着灯笼,在前带路。八位青年,抬着稳轿,紧随其后。三爷爷手里握柄秤杆,肩上背只木斗,跟在后面。队伍最后,却是随后赶来,举着灯笼火把的男女老幼。
不一时,喇叭凄厉,唢呐激越,两般乐器,竞相争鸣起来。二爷爷引领众人,上了坝头,队伍沿蛟河逆流而上。不出五里,却听坝脚下锣鼓喧天,又见那田畈上,灯笼火把,灿若繁星,只在黑夜里晃动。原来是曾祖母娘家得知了消息,满族人众,皆在等候相公菩萨到来。当下两姓族人合在一处,再向上游进发。又不出五里,眼见得到乌石堰了,族众们却早准备停当,远远迎了上来。一时间,锣声、鼓声、喇叭声、唢呐声、鞭炮声,响彻了整个乌石堰。灯笼火把宛如一条火龙,在大坝上绵延数里,将那黑夜照得亮如白昼。蛟河对岸人家,不明就里,纷纷起床,隔河相望,指指点点,议论不休。
爷的族里,闪出八位精壮青年,替换下汪家小伙,抬起轿一阵风来到爷家门前。丁道长八十多岁,仙风道骨,鹤发童颜。老道长领着七位徒弟,前来叩拜相公菩萨。爷依然躺在床上,人事不省。奶见屋里人头攒动,慌乱得不知所措。丁道长站在床头,手持朱砂笔,龙飞凤舞,画了张无人能解的符咒。一转身,将口水雾喷在符纸上,不一时,却见那符纸背后,鬼影交错,群魔乱舞,众人大惊失色。丁道长一扬手,符纸飞到半空,又燃着了。片刻,纸灰飘散,海晏河清。众人正惊奇赞叹,只听“呛啷”一声,丁道长从腰间拔出口明晃晃的宝剑,擎在头顶念动咒语:“头顶佛世尊,口念观世音。胸前李老君,胸后真武神。左有青龙将,右有白虎跟。弟子来到此,奉请护法神。”咒毕,转过身来,以剑指爷,大喝一声:“兵荒马乱,魂失泉台。受怕担惊,魄落长空。相公菩萨,护持众生。顷刻启程,为汝追寻。”七个弟子头戴道冠,身披鹤氅,扬起拂尘,异口同声怒喊:“急急如律令!”
二爷爷挑着灯笼,依然走在前头,爷的八个族兄族弟抬着轿子,紧紧跟定。三爷爷手拿秤杆,肩背木斗,走在最后。三姓族人闪开条路,举着火把,远远站在大坝上观望。只见二爷爷一行十人,抬着相公菩萨,直冲下坝去。那盏灯笼,一时飘在田畈上,一时又钻进了丛林,一时蹚过了小河,一时又隐入了村庄,一时光灿灿闪亮起来,一时黑漆漆不见踪影。三姓族人,不分男女,更不分老幼,站在坝上,齐声呐喊:“全忠啊,回来吧!跑山跑海回来吧!全忠呀,回来哟!走江走水回来哟……”一时间,势如惊涛拍岸,声震夜空苍穹。
再说爷家里,奶心焦如焚,丁道长领着徒弟,手里掐着诀,嘴里念着咒:“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缚魅,保命护身。智慧明净,心神安宁。三魂永久,魄无丧倾。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坝上的族人们整整呐喊了一夜,到四更天时,已渐渐困倦,老人孩子已然支撑不住,倒卧在坝头上,众人也渐渐焦急起来。突然,不知谁在黑夜里大喊一声:“回来了!”大伙儿顺势看时,果然,远远一盏灯火,游过夜幕,向坝上飘来。三姓族人抖擞起精神,老人小孩全爬了起来,一窝蜂向爷家门前涌去。不一时,二爷爷引着相公菩萨,从坝上飞奔而来,族人们如波开浪裂,闪出条路来。再看那一行十人,面色苍白,汗流浃背,如从水中上岸。
丁道长从屋里抢将出来时,三爷爷正把木斗抱在怀里走近。丁道长一把扯过三爷爷,疾步来到床前。丁道长猛一抬手,打落道冠,披散头发,仗剑念咒:“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队仗纷纭。朱雀玄武,侍卫身形。”咒毕,撇了宝剑,双手夺过木斗,高高举起,向爷砸了过去。同时,脚尖一挑,捞起宝剑,遥指着爷,暴喝道:“狼烟散尽,战火消弭。魂已回位,魄亦归身。全忠,全忠,还不醒来?”七位徒弟同声怒吼:“醒来!醒来!”
多年以后,奶说起这段往事时,仍是大惑不解。奶说那日四更时分,丁道长抄起木斗,劈头盖脸朝爷砸去,徒弟们又喊得山呼海啸,着实吓坏了她。但奇迹就在那一刻发生了。
爷昏睡了三日三夜,本已被许郎中吩咐准备后事了,此刻不知怎的,手脚却突然剧烈颤抖了一下,身子也跟着抽搐起来,只是眼睛还紧闭着。奶紧张地看看丁道长,猛扑到床边,大声喊道:“全忠啊,不打仗了,你回家吧!”话音刚落,只听得爷喉咙里“咕嘟”一声,接着如山羊般,咩咩叫唤起来。奶正不知所以,爷已慢慢睁开了眼睛。
丁道长仰面朝天,银髯飘飘,呵呵大笑,朗声朝着门外说:“全忠醒了。”众人啧啧惊叹,继而,皆涌到相公菩萨面前,不住磕头叩拜。丁道长吩咐二爷爷:“你们莫要耽搁,即刻请菩萨回庙。”爷的族众,放鞭磕头,恭送菩萨。汪家族人又敲锣打鼓,抬了轿子,前遮后拥,顺着蛟河,往相公庙去了。曾祖父和高僧们,在庙里自又是一番恭迎。剩下的这两众族人,喧喧嚷嚷,直闹到天放亮时,才各自散去。
5
家门前有棵大樟树,枝繁叶茂,冠如伞盖。皖西南夏日的黄昏,晚风徐来,爷常掇条小凳,坐在树下乘凉。那掉牙瘪腮的嘴里,叼了杆细长的烟袋。爷一边喷云吐雾,一边谈古论今,那些远逝的往事人物,又从浓雾里走来了。
爷说,当年他恍恍惚惚从黄泥港回家后,还没坐稳哩,那血淋淋的胡爷,死鱼眼的国军,便一个个浑身血污,悲戚戚、惨兮兮地朝他来了。爷直吓得冷汗涔涔,呵斥了一宿。次日清晨,好不容易睡了,又听耳边哭声不绝,昏沉沉挨到晚上,却看见自己闭着眼,横卧在床上。爷大惊失色,可喊破喉咙,只是没人理他。不多时,屋里屋外尽是人影,又听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时大惊,逃出了家门,只在那坝脚下的雾霭中乱窜。不一时却又听得坝头上,众人齐声呐喊,皆在呼喊他的名字,爷惊慌得哪敢答应?
就在这时,一个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的白面书生,从浓雾中飞奔而来。那书生跑得近了,也不说话,上前就来抓他。爷慌不择路,穿林渡水,四处躲藏,累得直不起腰,偷眼看看后面,那书生也气喘吁吁,豆大的汗珠,顺着清秀的脸颊,直往下滚落。但书生把红艳艳的长袍束在腰间,仍穷追不舍。爷已筋疲力尽,哪还顾得许多?见身后有只木斗,便一头钻了进去。
歇了片刻,又听得外面一片欢腾,爷想出来看个究竟,可斗口却被杆刻着北斗星的大秤封住了。正踌躇间,又觉得被人高高抛起,扔了出去,爷顺势奔跑起来,正跑着,脚下一绊,一跤跌进了黑暗的深渊里。爷正手脚并用,胡乱挣扎,耳边却听得奶说“全忠,不打仗了”,这才记起,战争早结束了,可眼睛涩得厉害,努力了几次,还是睁不开,情急之下,爷大叫起来,这才醒了。
随后不久,相公庙被三姓族人修葺一新,香客盈门,逢了节日庙会,那坝头坝脚,更是人山人海。这时,爷在乌石堰却连一天也呆不下了,爷说一到晚间,脑袋才挨上枕头,密集的锣鼓,顷刻间便响亮起来,那穿着大红袍的白面书生,自铺天盖地的呐喊声里,又飞奔而来。爷说,他整宿都在田畈上奔跑。
爷和奶收拾了包裹,顺着蛟河,回到了汪老屋。曾祖父为爷在蛟河大坝上谋了份护林员的差事。护林房离相公庙不远,爷每日早早起了床,风雨无阻,赶去庙里,洗净了手,磕完了头,给菩萨上炷香,这才驮柄弯刀,去巡视河林。爷沐浴着庙里传来的钟鼓梵唱,笑得舒心,睡得也踏实了。
6
多年后,爷故去了,相公庙也在原址上扩建了。每年春节,我皆要去庙里敬香。大殿上,相公菩萨红袍皂靴,金身庄严。那缭绕的青烟下,荡漾着乡邻们祥和的微笑。我的耳畔,恍惚又传来六十多年前,为爷喊魂那夜,族人们站在乌石堰渡口大坝上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