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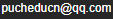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那是个如火山般喷张的夏天,喝口热水都怕上火的高温。阳光明目张胆地照在皮肤上,茂密的枝叶成了路人的大爱,风细小而无力地飘洒着。
我是大一新生。在很久很久的以前——初中时,我从不知道原来大学也是要搞这拿命的军训,所以当我听到大学是需要军训时,我炸毛了。
我拿着行李来到国防中心报到。为什么我会自己来到军训基地呢?因为我比很多新生都迟一天军训,简单点来说,就是我迟到了。在迟到的人中,有3名女生和好几名男生。而迟到的人都被安排在同一间宿舍,既然聚在了一起,哪有不聊天的道理,所以从这天的交谈中,我们三人成为了以后的好朋友。我替她们起了花名,一个较为娇小的叫乌卒卒,另一位清瘦点儿的叫落雨,(自恋一下:我很有才吧!)至于为什么这样称呼她们我也忘记了。
在为期两个星期的军训里,我参加的天数为6天,请假3天,装病3天,教官放弃我2天。虽然我旷了很多天,但还是认识了很多人,有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为什么不提这些人名字?因为在军训完毕后,这些人都作鸟兽散了,即使在同一个班。但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怡宝——冯欣怡(奸笑一下。)不过这是后话。
军训时吃的饲料那真叫不堪回首啊。中午是海带、冬瓜、豆芽,晚上是海带、冬瓜、豆芽,有时还会换一下菜式,那就是把海带或冬瓜换成猪红,豆芽换成大白菜,又或者哪天大厨良心未泯,觉得我们这群人是祖国的花朵时,就会放点猪肉——是全肥无瘦的肥猪肉啊。天啊,主啊,还让人活不?
教官们的座位在我们旁边,当你的眼睛去瞄一瞄他们的菜式时,你就会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分了。
记得有次吃早餐,十几人一桌就吃台上那丁点儿东西。大家都似乎很矜持,我却毫不客气,想吃就吃,而且是快吃,害怕自己手里这个没吃完那盘子里的都没了。后来在我的带领和渲染下,这桌子里的人都抛下了淑女之态,快吃快抢。我这人只吃面包或蛋糕,那些白馒头、肠粉啊都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但只因这群人吃得太疯狂了,把我的蛋糕一下子就秒杀掉,我心,悲痛啊。要想前段子我可是能吃三个蛋糕的,而现在却缩减到一个了。我吃不饱,所以必须要改口味了,吃肠粉。白花花像豆腐一样颜色的肠粉让人只想反胃,于是就去阿姨那里打酱油。阿姨舀了一大勺给我,我立刻受宠若惊的连说够了谢谢啊。她还想再舀,我摆手不要,心想:想咸死我不成。将酱油倒进肠粉里搅拌了几下,吃一口,咦???没味道。我将此情况告诉同桌人听,她们都告诉我:酱油掺水啦!TMM的,我怒也!想我们拉肚子就直说嘛,耍什么阴招。孟婆的汤都不掺水,你这酱油搅什么乱。
从此以后,我拒绝像豆腐的肠粉!
实验证明,我的拒绝是对的。话说那天大家都很安静的在吃早餐,乌卒卒她戳了戳我手臂,等我看向她时,她又指了指那碟豆腐肠粉,然后很小声地跟我说“……。”我没听清楚,只看见白皑皑的景物下隐藏了一只褐色的身子,我凑前一看,不敢用筷子翻,问在台的人“这是什么?”有人闻言,用筷子揭开重重包围的物体,一只肥美而恶心的蟑螂暴露,它无力地躺着,事实证明,它已经死了。为它默哀2秒,下世得做人,偷吃不偿命。有人向教官反映此举,教官神情潇洒,看了看,说:“没事,正常。”就走了,碟子还遗留在我们面前。给予这样的回复,我们气爆血管,身体似乎受到记者的蛊惑,非常专业地拿出手机拍照、上传、发微博。
我窃喜,没事,没事,我真的没事,你们也别有事,以后生出来就行了。(别人大骂:你脑子秀逗啊!(是陈述句))
带领我们队的那教官第一眼没啥,但看久了就觉得欠扁,这是经过我们队将近全体成员的官方认可。他那双眼睛就好比讨人厌的呕心苍蝇,专盯着皮肤好的女生。他想养眼不要紧,但拜托也要看场合,好不?别老是娇声细语和那群女生叽咕嗲气,你要养眼,我还需暖胃呢!
经过如轮回般千转百转的调位后,有个女孩她站在了我旁边。第一眼看到她时,我愣了下,但其实我认错人了。我以为她是我实习时的一个同事,她们的眼睛太相似了。因为在调位之前我们没有过言语交流,所以我不可能一看到她就像那些小痞子泡妞般跟她说:“你长得好像我的谁谁谁。”这种认识方式,让人觉得虚伪和倒胃口。我不喜欢别人说我什么东西跟别人像,因此,这个想法我强加在她身上了。
站在前后左右,哪有不聊天的道理,因此在后来的聊天中,我知道她叫冯欣怡,自诩怡宝。因为她这个别称,我和乌卒卒列举了很多矿泉水的名字,如景田,统一,冰纯,农夫山泉,哇哈哈等,乌卒卒要了冰纯,我想要农夫山泉,但名字太长了,所以我不允许乌卒卒叫冰纯,我要她叫山泉而我叫农夫,当别人一叫农夫山泉,多悦耳!
话题扯远了。与怡宝接触久了,也不觉得她像我同事,只是外眼角有点上扬,就像李玟的那个外眼角微微上扬,以至于让我产生了错觉。不过咱家怡宝的眼睛比李玟的大,少火辣。
开学第一天,各回各班。怡宝和乌卒卒是人力资源系在北校区,落雨是英语系在本校区,而我是管理系且走读生在北校区,那些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与我同系,但似乎只乐于和同宿舍人一起,所以我也没和她们多呆。
老师开了门,属于坏学生的后排座位一下子全被占光。我进得比较晚,所以后排位置我没得选择。好吧,既然老天想我当个好学生,那我也就只好屈全了。我用眼睛扫视了一圈,选了第二排的第二个座位。这些桌子都是相连的,如果我想进去第二个位置,那第一个人是需要站起身来让我进去。我站在第一个位置的人的旁边对她说:“我要坐里面。”我指着第二个位置,也就是她的隔壁。我以为她只是欠欠身让我进去,谁知她却自己坐进去了,我当时有点傻场。后来当我回过神来时,觉得她这人心地不错。既然都坐在了一起,哪有不聊天的可能。她说她叫少玲。
少玲有个室友,她室友经常迟到,我经常笑话她,但她自己却说:“主角都是最后上场的。”所以很理所当然,主角成了她花名。
在这一个学期里,我们(怡宝和乌卒卒的课程与管理系相同)就坐在了好学生的位置上。大喊一声:我们是,五人帮!
紫荆花铺满在青绿色的石砖上,恶劣的空气荡漾,积满灰尘的暗绿色叶子无声摇曳,街道上走过一个个无比生疏的陌生人。
我们五人颙望阳光,一起手挽手踏过满地紫荆花瓣,品尝廉价而美味的3块钱粥,口里叼着让人觉得恶心的绿舌头,闲着没事去捣乱计划生育的箱子,光明正大地看着隐藏在树荫下亲吻的男女,用鄙视的目光杀掉像妓女般高姿态低行事的女生。
我们嘻嘻哈哈地混着日子,迷迷糊糊地沉浸在时间里,配合着文明城市的招牌套上人模狗样的淑女伪装。
我们是18、19岁的年华,天顶着一片汪洋的蓝天。带上青春,系上友谊,看着彼此童真秀丽的脸蛋,展开巨大的羽翼,为情谊喝彩。
手臂上的友谊,牢固而结实,它靠近心脏,最能了解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