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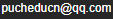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说再见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再次相见
我想再次见到你
因为害怕离别的忧愁过于汹涌
让我失去自我所以我说再见
然后我们真的再也没有相见
有些事情她已经很久不想起了,也想不起来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那天记不清的是什么事。晚上11点坐公车回家。坐的事车后的双人座,靠窗位置,窗户打开看,一股股的凉风急着想弄乱她整齐的发丝。她随口哼起一首歌,哼着哼着车子猛一刹。司机本想闯黄灯的。她舒了口气,想继续拾起那首中断的曲子,却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了。可是突然所有那个夏天晚上的感觉都潮水一样的涌向她来,涌的她兴奋的慌,想抓住它们,唯恐它们跑掉了,跑掉了。
一样11点钟的九月晚上,一样的公车位置时一样的路,车也开的一样的快。那是她才跟同学们看完场电影回家,都是女孩子,也谈不上谁送谁回家,只是自顾自的分了道,似乎从未认识。她哼的是那场电影的主题曲,愈哼愈觉惆怅。看着寂静的红砖道,听到身后零零碎碎的脚步声,不禁有些慌了。她屏着气,没敢放松脚步,更不敢回头,但到底还是被他赶上了。一侧头,便看清了侧脸,是她的后桌,不由的松了口气。
他个子高,腿长,走一步抵她两步,他没跟她招呼,就跟她并肩走着。只见他两手悠闲的插在口袋里,散步一样,相比之下,她小小急急的步子倒显得在负气似的。一开始就注定她是赢不了他的!
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她扬起眉睫含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轻扬的语气像一个极度友善的女孩子。
“阿泽。”她这才知道他的名字。原来两人刚做前后桌一天,仅仅只能辨认出对方是自己的前桌罢了,下去他并没有反问她的名字,所以他也没有再说话了,她坚信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正如她坚信他不是在送她,只是两人同路,恰好搭同路车。
等着车的时候,他也还是不说话,两只手始终不离开裤口袋。头微微仰着,似在看什么,那晚的月亮很好,路灯一样的亮,然而他并不是在看月亮。
她站在那儿。忽觉得双手没了去处,本也想放口袋里,却觉得自己平时并不曾把手往口袋放,于是在那绞着手指,感叹手好好的怎么就碍着自己了。
车来了,她上了车,回头望见他并没有上车的意思,便摇了摇手说:“阿泽再见。”
顿了顿又接了句,“我叫若若。”无奈在讲后半句时,车门已经合上,她并不知道他是否听到。
她是生于江南水乡的人,也取了个温婉的名字,夏若若,但却不是什么腼腆柔和之人,自然也不会介意和男生聊天,只是到底太过于生疏,所以一路上也没说几句。
只是两人熟了之后,又是另一种场景。
“喂,借我支笔。”他毫不客气的从她的笔袋中翻出支新笔。“喂,这是我新买的啊!”她张牙舞爪地扑上去,欲夺过他手中的心爱之笔。“别那么小气嘛,大家同学一场。”他的手举得高高的,那只笔正夹在她那两根纤细的手指间。在一阵努力无果之后,她气愤地插着腰。指着他:“你怎么每次都这样,总是问我借笔。还总是借新的,写一次又不要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小脸气得红涨,相较于她的气愤,他显得悠闲多了,安然地转着笔,听她“泼妇”般地骂着他,等她骂完了,又佯装不耐地驱赶她:“安啦安啦,大不了放学请你吃冰淇淋!”她顿时气结,又不甘心地做最后的抵抗:“这是冰淇淋能解决的问题吗!你……”依旧是责骂,但气势大不如前,明显已被冰淇淋收买了,再低头看他,早已埋头做题。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她那么低,那么低。
班里换位置,她让他帮自己搬下桌子,他喝着可乐,摇着头。“你怎么这样?怎么就有你这么懒的人?!”他依旧喝着自己的可乐,不抬一下眼皮。她狠狠踹了脚他的桌子,然后又抱着脚一跳一跳地去找别的男生帮忙了。她就不信,这么大一个班级,还会没有人帮自己。来人看了眼,说:“不是有阿泽么,怎么不叫他帮忙?”忽的抬头,看见某女正用极凶悍的眼神瞪着自己,忙闭了嘴,赶紧干活好离了这是非之地。
他倒也非一无是处。
在篮球场上来回奔跑,挥洒汗水,带领班级拿了许多个第一回来。她总会在他比赛时,在一旁大喊:“阿泽!加油!”他的名字平时总被她用“喂”代替,也只有在比赛场上才会喊。而每每这时,他也总会回过头来,对着她咧嘴一笑,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中场休息时,她递瓶水给他,他笑笑,接过去,灌了几口,道:“等会儿喊响点啊,都听不到!”她佯怒,抬起拳头狠狠砸在他背上。他装作吐血,一边又埋怨她不像个女生。是啊,她本不是个合格的女生,她总是在男生堆里更混的开,时常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着啤酒,这是其他女生所不能接受的。
“喂,你就不能像点女生,你看别的女生成天拿个镜子照啊照的,你在干什么啊?”他转着笔,笑着看她。“切,要你管!”她不屑的撇过头。“小心嫁不出去哦~”他说完偷笑着低下头去写作业,一边又竖起了耳朵,果然,听到了她的磨牙声。结果?结果又是他的冰淇淋摆平了她啊。
这两人就像是对冤家,成天吵吵嚷嚷,倒也不清闲。
转眼,3年过去了。高考结束,班上一群活跃份子吵吵嚷嚷着,非得弄个散伙饭。
酒桌上,一群男生喝醉了酒,拿着酒杯要和她拼酒。她一拍桌子,毫不客气地接受了。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不一会就醉了。路上,他送她回家,他扶着她蹒跚地走着,她时而唱几句歌,时而又喊着干杯,满嘴的酒气充斥着他的鼻子,双手努力想按住不安分的她,却又无济于事,屡次被她挣脱。
等到上了公车,他终于将她按坐在座位上。股股凉风终于将她吹醒了些。她眯着眼斜目看着身旁忙的焦头烂额的他,一遍遍地重复着,阿泽再见!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这次再见竟是永别。
几年后,当大家再次聚首时,独独少了他。她环视了一遍周围,发现没有他的身影,于是叫住他曾经的一个好友,而对方只是摇了摇头:“只是听说他去了国外,不知道他去了哪国。你也不知道吗?”她笑了笑,他的事我怎么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这么低这么低,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她必输无疑,现在连他走了,也不肯告诉她。
晚上她又和同学去看了场电影。11点时,依旧独自一人走在红砖道上,她多希望身后能响起他零碎的脚步声,可是没有了,没有了。
跑掉了,一切都跑掉了,她再也抓不住了吧。
坐上同一辆车,坐在同一个位置,依旧是九月的凉风一股股的想弄乱她整齐的发丝。一切都好像那么熟悉,天空钟星星依旧眨着眼,那样一个夜晚,一路上灯光总是趁势一框框的跳进车子里,空旷的车厢地像是一幅银幕,路边的树影落进来,三五根平行的电线。像是在放映一部长长的片子似的。她有心无心的看着,想起许多事情来,原来他们竟是这样,胜过友情却又不似爱情。
她不晓得为什么从一开始她就那么的低,却又时时有千般无奈,像是委身于他似的,其实这也说不上,他对她是顶好的,这个人,他不讲,他没讲,她都突然晓得了。
她起了身,准备下车,突然看到自己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映在门玻璃上。
是了,她记起了阿泽的眼睛,那样含笑睁着,她的影子在他的瞳孔里活起来,那一刻把她的本命给逼出来了。
她咬住唇。点着头,在心里一遍一遍低低说着,我晓得的,你放心……玻璃上的人影模糊起来,被一层云气湮开了,她知道自己哭了,突然激情起来,几乎要一叠声地喊出来,放心……
她就着车门的第一个位置坐定下来,这灯光仍然一框一框的跳进车里来,这会儿她头发被风吹的一撩一撩的影子竟落在前头地上,倒又像在看一场长长的电影了,然而她是个恒久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