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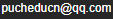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冷漠的秋风肆无忌惮地吹黄树上残余的绿叶,淡淡试试寒风,裸露的肌肤有种被划伤的疼痛。人们换上了些能使自己暖和些的衣服。天气过于干燥,一丁点雪的影子 都看不见,妹用额头顶在车玻璃上用哈气画小人,本是白白热乎的小手不一会儿便冰冰肿肿的,妈心疼,只好把她抱得离玻璃远一点儿,让她去摸索我的手机游 戏……不过倒也让这具着“不怕死,怕死不是共产党”精神的小“刘胡兰”安静那么一会儿……那次的目的地是老家黑山,当时还小,回那的次数颇多一些,就像 “对不起”说多了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一样。坐在开着暖风的车里,冷意也挥发不少,犹记几年前“黑山”这位老大爷的模样,空气中都弥漫着淳朴的土香,家中不 至九点无人归还,品茶的,说书的,溜达的,打扑克的……干什么的都有……儿时我还记得三爷骗我说山上有兔子,倒也去抓了,只是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找罢了,大 概是没有的,小溪都冻得结实,这也是哄我开心吧。老家离矿场不远,大姑父就在那工作,我曾坐在他肚皮上看过几年的“动物世界”,他去世十年了,那时我才五 岁,他走的时候,我竟一滴眼泪都没掉,后来爸因此事差点将我打死,回想起来,那时我还太小,哪知道大姑父不回来了,只感觉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毒打。现在正是 正午,却一点要温暖的意思也没有,我们四人一路上吃了一顿饱饱的“颠簸”,偏偏赶上修路,一下车感觉原地满血复活般舒爽,爸检查完车子跟在妈后面,妈跟在 我后面,我又跟在急着去追蝴蝶而疯跑的妹后面……大约舒展了五分钟,妹被爸夹在腋下,露出一种极度失落而低谷的表情,如果她吟出一句“腋下舒展难,难于上 青天。”我肯定赏析的妥妥的……“哎呦,这不是霖子吗。”“是呦,这么高啦,一米八几啦?”“还记得我不,我是给你冻冰块的杨姑!”十年前人家见到我和我 爸都说:“老王啊,这你儿子啊”十年后一看见便改为:“哎呦,霖子,他是你爹啊”妹一回家便跑出去与小孩子们玩耍,我这也乐得清闲,小家伙把我手机玩的一 点电都没有,不要眼睛了吗?家中的棉被在阳台受了一天的阳光浴,一趴上去就有种温暖的味道。妈出去陪妹了,爸在门口抽烟,二人看见我在床上摆出一个“大” 字,轻笑的忙自己的去了。我的思绪跟着那遥远的山头的风儿飞了出去,飞到了十万八千里远,飞到了一个地方,好像是…我的以前……黑山有种职业,不,乞丐。 人们都管他叫“江五”,他是专门行乞然后拐卖小孩的坏人,会编故事的老人都把江五形容的鬼神一般,就在不远的过去,我就 差点被那双肮脏的双手糊走……那时是夜晚,萤火虫都已熟睡的时间,爸爸与我闹脾气,他说我吃饭漏嘴,因为还小,喂饭还不好好吃,爸就“稍微”管教了我一 下,我就全身“红吻”哭着夺门而逃,天气很冷,自己的只剩下一件小秋衣裤,也许是哭的,忘记了寒冷,跑着跑着来到了广场的医院旁,正哭走着,听见有人 “嘿”,转脸一看,那人正坐在井盖上取暖,一身烂衣,破烂王一个,用那脏兮兮的手招呼我,那个头发好似个大菜花,蓬蓬的不知几月没剪,更别说洗了。我自然 知道是谁,腿就止不住的哆嗦,我不敢过去,就呆呆的看着他往我这边爬……好似个泥鳅蠕动着,接近我时,嘿嘿一笑,露出了那一排口齿不整,黑黄不等的牙。我 “激灵”一下,哇哇哭起来,接着一场跑酷就开始了,只是我跑没多久就撞爸爸怀里了,爸爸当过水军,自然不虚他那狗腿子般人物,把那江五打的活像个“大尾巴 豺”。回到家,我小脸吓的苍白,呆若木鸡,雩雩伫立着向屋挪,爸把我抱起,让我坐在他的臂弯上,家里就我俩,他这是第一次喂 我吃饭,才知道都是他喂撒的,喂完后,不是忘了擦嘴就是忘了拾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的衣服脱掉上药。睡时睡不着,邻居家有条狗疯叫着,他在我屁股上涂 了三倍的药,而且不会哄孩子,学妈妈哼歌拍我睡,歌哼的不错,但每一掌拍下来都让我差那么一口气,我也不知怎么睡的,只记得妈很晚才回来,她被吓哭了,抱 着我碎碎的念叨:“这要让人抱走了可咋整”我只想睡觉,没理会他们,一翻身睡去。、情景又回到了今天,我这么大了,没有江五来抱我,量他也不敢招我了。我 们在黑山待了五天,走时恋恋不舍的道别,阳光洒在我的身上,说不出是温暖还是寂寥,乡间传来稻草人吓乌鸦的声音,轿车走着,人乐着,与此同时,道口出现个 人,木木的走过去,不知为何,阳光突然灿烂起来,照亮了那个人的笑脸,是那个江五!!!后记:未来是用来想象的,记忆也是会忘却的,不要失去了才懂得珍 惜,不要等镜碎了,再去想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