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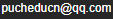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这是个极为平常的早晨,我和许多人一块儿在车站等车。朦胧的晨雾让我不由得感到一丝压抑,人们都睡眼惺忪,沉沉的回味着昨夜的好梦。车终于来了,因为是冬天时节,正如料想的那样,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硬着头皮上车。我跟在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后挤上了车。男子有点步履蹒跚。这个男子很魁梧,他左手提着袋水果,右手拎着个包,还用身体护着前面的一个带网球帽的小男孩。他的动作像“老鹰捉小鸡”中的鸡妈妈,撑开双臂努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我们挤得有点艰难,刚一上车,就有人给他和孩子让了座。我顺势站到了他的旁边。“爸爸……”只听见一种很沙哑、难听、刺耳的声音。我忍不住侧过头,看着孩子吃力的样子。附带着几声咳嗽。他肯定是个发生器关有问题的孩子,他用尽权利使劲地振动声带,发出即不标准也不动听的“爸爸”声,他的嘴巴奇怪的张着,下巴上还挂着一条长长的口水。而那个爸爸一直微笑着看着孩子,不时地在孩子的下巴上抹一把。“爸爸——”还没说完,又咳嗽了几声,“你吃——”孩子拿着一只梨一定要爸爸咬一口,明亮的双眼注视着爸爸,红扑扑的脸让人心醉。“乖孩子,爸爸不吃,你吃吧。”爸爸边说边给孩子擦嘴,还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头。他们就这样旁若无人的说着话,丝毫不在乎别人投来的异样的目光。我忽然想起曾经举行的“残疾人士”用心灵的表演,他们在台上毫无紧张感,每一个动作都做的全全一致,用心灵带给我们最诚挚的微笑,最诚挚的舞蹈。他们虽然是残疾,但有什么理由说他们是那白床单下的奄奄一息的病人?我想:他们是最有诚挚的人。“爸——爸,车——”孩子又说话了,他兴奋地用手指着窗外那花花绿绿的车辆。车辆很多,构成了一幅长长的画,看不到其头,也不见其终极,毫无秩序的散在路上。“那是轿——车,那是摩——托——车,那是大——货——车。”爸爸慢慢的告诉孩子,一一指出车来给他看,欣慰的笑了。“大——车。”孩子学着说,虽然吐字不清,但还是勉强说了出来。“大——货——车。”爸爸又放慢了发声的速度。“大——货——车,大——货——车。”孩子跟着念,认真而又吃力地重复三五遍后,又扭头看窗外了,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灿烂,散发着无限稚嫩的童心。站在旁边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或许是在为上天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或许是被这对父子的言语而感动,这么一个充满善心的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悲惨遭遇,胸腔中不知怎的一下子涌起难以名状的情感。一路上孩子不停地发着那种奇怪的声音,几乎所有的字都吐不清楚,唯有“爸爸”的叫声充满了自信和力量。这叫声充满了我的耳畔,那样响亮那样震撼人心。一下车,我不自觉得回望客车,一只大手抚摸着一只小手,大手雪白白,小手红润润——心灵之花总开在绿叶中,是那么快乐真实,平静而幸福……车开走了,阳光温暖的让人心醉,回味着那嘶哑奇怪的声音,温情的笑意溢满嘴角——那一刻,我确信我看到了心中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