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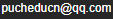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阿太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这是第一次看见阿太杀鸡时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阿太是奶奶的妈妈,自我有记忆开始,阿太已经是满脸皱纹,容颜只是依稀可辨,很大的时候我才从奶奶那里看到阿太的照片,泛黄的照片看得出阿太年轻时是个美丽的姑娘。那个年代,阿太能留下自己动人的照片,我疑惑的问奶奶阿太是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奶奶叹了口气:“小姐,地主家的小姐。”
我起初并不喜欢阿太,不喜欢她走路的姿势,一双三寸小脚吃力的跨步,让人看着很是揪心。如若这样,阿太在别人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时应该感激并接受帮助,然而阿太却从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协助,就算接受了帮助也绝对不会去感谢。我不解就算是小姐也贫穷了几十年的阿太为何还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姿态。然而看法的转变有时只要一个瞬间。
那天清早,初起床走出门,看见雾蒙蒙的井边一个小脚女人吃力的抓着一只鸡,也许阿太是真的老了,手上的鸡拼命的挣扎,阿太不好下手。这时她看见了我,吆喝“丫头!过来!”我跑过去,接住了阿太递给我的鸡,那是只很肥很肥的老母鸡,我抱着它像抱这个婴儿。“一只手抓脖子,一只手抓脚,你这么抱我还怎么下刀?”阿太不紧不慢的说出这句话,我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双手颤抖着按照她的意思做。母鸡在我手里没有挣扎,阿太割开母鸡脖子的一刹那母鸡垂死挣扎了几秒,就再也没有了生命的气息。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消逝只需仅仅几秒钟。不知为何我对心狠手辣的阿太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后来阿太问过我,母鸡挣扎的时候哪来的勇气手抓紧它不放,在她看来这个年纪的小女孩应该十分胆小,这些都是后话了。那一年,我五岁。
渐渐长大后,上学成了我不得不离开家乡,和阿太分别的缘由。幼儿园在很多地方还被称作幼稚园。第一天去幼儿园,看着一群女孩子哭哭啼啼不愿意和妈妈分别,抱着洋娃娃哭泣,对着洋娃娃说话,脑海里浮现出阿太冷冽的表情和一声没有感情的“幼稚”。与母亲告别,认真听老师讲课,午睡不发出声音,我被老师表扬懂事,在她把小红花贴向我额头时,脑海里那张阿太冷冽的脸突然变得慈祥。那一刻,我渐渐理解阿太为何从不奢求他人帮助。如同那些离开母亲的小女孩,抱着洋娃娃哭泣终是无济于事,有些事,只能靠自己,朋友,亲人也终有一天会离开你,就算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他们的帮助,你也必须坚强的独自活下去。
幼儿园毕业那年暑假,接到奶奶的电话,我不得不赶回老家。听说阿太快不行了,一直想再看我一眼。
**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一次见先生,他穿着暗蓝色的长衫。我让钟叔帮我去请先生给我做私塾先生,可是先生拒绝了,几次三番后,钟叔也劝我就罢了,折腾也没个结果。不甘心的我苦苦请求了很久,爹终于同意我转去学堂读书。认认真真的听每堂课,认认真真的看先生写的每个字,先生时常会对我点点头。不久后我生辰那天,在所有女同学的推搡下,终于红着脸把写写改改很多次的信悄悄先生的公文包里。次日先生只和我说了一句话,那以后先生便离开了学堂,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当时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后来回想起来,也许果真是我错了。那天先生只和我说了一句话:勿施于人。
父亲匆匆忙忙把我送回老家,直奔向阿太的房间,却不见阿太的人影。在头脑一片空白后,身后传来阿太的声音:我没死。就当是虚惊一场,阿太的确完好的站在我的面前,目光还是那样的高不可攀,仿佛我对她的关心是一种错误。阿太的确突然病倒,也的确几天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做所有人看来阿太都是时日不多,然后久久不愿咽下最后一口气只是为了等一个人,长辈们很快便想到我。可是阿太却在我回来的那天早晨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正常的起床打井水,在很多人诧异的眼神下,阿太冷淡的说了一遍又一遍:我没死
**那天娘被人带出去,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着,摸着我的头发说:丫头,这都是命。第二天早上娘就被人从河里捞上来,娘死了,她跳进河里死了。没过多久,学堂里的学生一个一个变得疏远我。我被她们推进河里冷的哆嗦,幸运的是,我又看见了先生。先生拉我起来问我怎么被欺负不知道跑,我没说话,先生叹口气,突然认真的看着我问我:我要走了,你可愿意等我?
回到上海后,我进了小学,快乐的时光都是短暂的,时长五年之久的小学转眼要毕业了。那日大家一同写告别母校的作文,上交后,老师把我叫去办公室,“你的作文写得很好,想把它作为材料在毕业典礼上朗读”我欣喜的点头,然而她却又说:“我准备让邱尧来读,她经常上台撑得住场面。”这句话让我没有任何反驳的权利,我很想质问:既然已经决定了叫我来办公室只是为了告诉我,我的作文将要被冠上别人的名字?可是我没有问,点点头说,好。
毕业典礼上,她读着我的文章,看似经历了我的故事,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憋屈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在别人看来,那是女孩子即将毕业舍不得母校,依依不舍而落泪。
回家的路上,一路擦干眼泪,感谢当时的自己没有在办公室与老师翻脸,老师本就是对的,也许我上台演讲,会发抖会怯场,这么庄严的典礼一定要把班级最好的一面献给所有人。也许很久很久以后,也不会有人再记得毕业典礼上发言的那个叫邱尧的女孩子,但是能肯定的是,很久很久以后绝对不会有人再记得我,也不会有人知道演讲词里的故事出于谁笔,但是只要慢慢的文字已经被认可,那已经是对文字最好的褒奖。人应该学会满足,有些事也许真的不用去解释,就像阿太的那句冷淡的:我没死。已经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先生走了,去哪儿了,大概很远的地方吧,他没有告诉我,我便也没问。可是不久后,出了一件大事,我不得不违背与先生的约定。后院在某天夜里突然失火,钟叔和爹把火扑灭后,爹扑通一声跪在钟叔面前:“老钟,这么多年,只有你还留到最后,求求你,求求你把丫头带走吧,求求你。”钟叔扶起地上的爹,然后问我:“你肯嫁给水生吗?”父亲老泪纵横的脸,让我没有任何拒绝的借口,我点头。我就这样被钟叔带走了,也就这样嫁给了钟叔的儿子水生,也就在这样的不久以后听说爹被人带走,听说爹和娘一样永远的离开了。
**水生是个肯吃苦的人,也不舍得让我干活,时常傻傻的问我他的名字怎么写,他爹钟服川的名字怎么写还有他娘的名字,水生是个老实人。这也是上天对我的厚爱了吧,若不是水生,我恐怕早就死了。以前的大院被烧了,我从衣食无忧变成了手上开始长老茧的普通女人,水生家分到了三亩田,日子渐渐好过了。平淡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先生,想起先生的话:你可愿意等我?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和水生有了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
初二那年的冬天,我靠着阿太的肩膀问她:“阿太,上次他们说你不行了一直咽不下一口气是在等我吗?”“不。”阿太回答的很果断,“我在等先生。”“先生是谁?”“是阿太活下去的念头。”“阿太喜欢先生?”“怎么说话?没大没小。”“那,阿太,你,和太爷有爱情吗?”“没有。”阿太的回答意料之外的平静。“为什么嫁给太爷,不嫁给先生?”阿太不说话了,细着眼睛看着远方层层叠叠的山峦,稍稍动了一下嘴唇,我没听清她说了什么,也不想问了,只是陪着她一起看着远处的群山,阿太以前经历过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她心里有个盼头,老人就满足了吧。
**先生再没有回来,也许不会再回来了。我时常问水生:“勿施于人是什么意思?”水生憨厚的笑笑:“我的媳妇诶,我都不识字啊,啥勿施于人的字怎么写我都不知道。”也许水生知道我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先生,但是水生从来没有提过,我嫌弃过水生大老粗,有时没法和他好好说话,稍微有学问的词水生就什么都听不懂了。可是我这条命都是水生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嫌弃水生。日复一日,子辈们都长大成人;年复一年,我到了做奶奶的年纪。我深刻的意识到我老了,水生早一步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不爱和孙辈们说话,有时他们说的我根本听不懂,有时看不惯娇娇滴滴的女孩子害怕小虫子。
**那天是水生的生辰,纵使人不在了,我也想给他杀只鸡,去坟头给他倒杯酒,我不喜欢在祭日干这些事,太过悲凉。人老力不从心,我抓不住那只鸡,远处看见一个姑娘直直的看着我,是大女儿水仙的孙女,我吆喝她过来帮我抓着那只鸡,她走进,我就后悔了,瘦小的黄毛丫头大概连蚂蚁都捏不死,让她抓着鸡,她倒好,把鸡当宝,抱在手里。让她一手抓着鸡脖子一手住着鸡的腿。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我小看了这丫头,她胆儿大得很。下刀后,鸡死命挣扎,丫头竟然都不放手,和我真是有几分神似,我喜欢这个小丫头,很干净,让很看着踏实。
初三临近中考接到奶奶的电话,阿太不行了。的确,阿太这次大概是真的不行了,阿太真的老了。父亲和我说:“回去吗?要中考了……”我摇摇头,“阿太,不是在等我,上次也是,这次也是,不是在等我。”父亲点点头:“那好,那就别回去了吧。”做着一道又一道题目,我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就像当初母亲总说有人在叫她,不久后,母亲的爷爷就去世了,我的的确确听到了阿太的声音,眼眶莫名红了,“爸,我想回去,我想看看阿太。”父亲诧异的看着我,还是点点头,“好,明天周五,明天你放学我们回去吧。”事情总是突然的,次日早晨就到消息,阿太,走了。我终是没能见阿太最后一面。
**早就一生老骨头了,早就该随着水生去了,不服老,又不得不服老,我好像快死了。一直到死,恐怕都等不到先生了。我还能活多久,这次那丫头还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冲来看我,笨丫头,我哪里是在等先生,确切的说,是我也以为我在临死最后会想着先生,可是,潜移默化里,总是会想起你,临死前的最后一刹那我的的确确是在等你啊傻丫头,阿太最舍不得的,是你,上次阿太就该死了,从阎王手里偷回一条命,这次,不会那么幸运了。恐怕等不到你了,恐怕你不会来了,阿太走了,你要好好的。
雾蒙蒙的清晨,那个记忆深处的老妇人,一手抓着鸡,一手举着刀。我终是没能再见你最后一面。
你可愿意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