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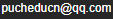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周一,虹姨要去听课,迫不得已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
为了保证钥匙的安全性,她用红绸缎穿过钥匙底部的空隙,形成一个大圆形,打好结,钥匙可沿着绸缎做360度的滑动而不离绸缎。
我家有姥姥、虹姨俩位长者,平时她们总有一人留在家里为我守门,偶尔有急事外出,姥姥也不让我碰钥匙,最多就是让我与虹姨同行,不想去也得去,由不得我。
长期以来,我以为佩带钥匙者就是家里的统治者,执掌着家里每个成员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权。她们拥有至高无尚的领导权,时常对被统治者、被管理者进行着压迫,而且是随心所欲。
今天,我终于佩戴上了进出家门的钥匙,成了一个小小的统治者,可以对姥姥和虹姨发号施令了,尤其可对长期压迫我的虹姨出口恶气,心里好愉悦呀!
我把钥匙戴上,躺在沙发上,一手拽着钥匙,一手顺着光洁的绸缎带上下来回滑动,得意忘形地设想着没了钥匙的虹姨回家的种种狼狈样,以此衍生的制裁方案。我憧憬着,美好着。
想得差不多了,我跃身起来,把沙发整理好,拉开门,先伸脚,再跨身,转身把门关上,一蹦一跳地下楼玩去了。
玩够了,上楼,把钥匙插入钥匙孔一转,门开了。我自豪地走进家门,再顺手并上门。因为没有往日“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式的审问,整个感觉好极了。
晚上,“咚、咚、咚”,是虹姨的敲门声。今天我作主审官、统治者的机会终于等来了。
“您怎么才回来?课上得怎么样……”我把门开了一个不宽的缝,探着头对门外的虹姨说。
“老师讲到六点十几分才下课,从省委党校到玉林的路又堵车,所以才回来。上课是认真的,有笔记为证”。虹姨无可奈何地说。
“那我检查笔记。”我不依不饶地说。
虹姨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双手递给我。
我宏观地翻了一下,记了十几页。初审过关,开门放行。
虹姨进家后,放下手中的包,马上进厨房忙碌起来。洗菜、切菜、做吃饭,不亦乐乎!
我则继续扮演统治者的角色,边看笔记边问不懂的内容,家里所有的成员都处于和谐之中。
……
三天的统治者生活就这样一眨眼过去了。
今天周四,虹姨不再去上课学习了。上午8:00时我起床后,虹姨笑咪咪地对我说:“妹妹,请把钥匙还给我。”
“笑里藏刀,给。”我一脸不悦地将钥匙扔给她。
“别不高兴,下次我去学习,又把钥匙给你。”虹姨认真地说。
“嘿”,我使劲地哼了一声,看都不看她。
“你当了三天家,今天该我执政了,轮流执政嘛!”虹姨说。
“轮流执政,不利于政绩的巩固!”我猛地提高嗓门儿叫。
是呀,我需要执政、需要握有一把家里的钥匙、需要自由地进出家门。这是我的基本要求,也是我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