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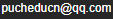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眼,蛇年好像还没品出味来,就已到年尾了。大凡人们心态上有个习惯,每年到了秋末,就远远地遥望春节的身影了。剩下的时段,好像快速行进中的列车,下一站就是终点一样,旅途的人们开始舒展一下筋骨,拍打一下尘土,紧里慢里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最终的期待是回到温馨的家,然后在春节那几天,有钱没钱的都安下心来,享受一下阖家之乐。
在这个星球上,凡是和“汉”字有渊源的人们,是绕不开春节的。春节和他们的血液一样,是鲜红鲜红的。春节前,穷也好,富也罢,人们想的都是如何过好自己的春节。传统上,打扫一下房间,为孩子们准备新衣,把一年欠别人的和别人欠自己的账目结清,然后贴个对联,请个门神,放挂爆竹,则是必须要做的事。至于明年如何活法,那是过完年后操心的事。所以,人们在节前都爱说的一句话是,“管他娘的,过完年再说。”
由于人们对于春节的情结这么浓郁,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串自己过节的故事。我觉得春节的故事是最有人情味的,是最具有生活本色的,每个人讲起来都会声情并茂,那是一边回忆一边品味的诉说,而听的人,也会一边听,一边回味自己过节的点点滴滴……
而今,我已步入半百之年,屈指算来,也算过了五十多个春节了,五十多个春节,年年新桃换旧符,换来换去,都没磨灭我对大半生的春节记忆,不同时代的过节往事犹如昨天。细细品味,对于往昔的春节年味变化则唏嘘不已……
也许是人老怀旧的缘故,我对儿时的春节记忆特别清晰。
记得我人生第一个有记忆的春节,是在60年代初的五一农场。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母亲早早的把几个孩子喊起来,抱过来一堆花花绿绿的新衣服给我们穿上。洗漱完毕后,发给每人两个染成红色的煮鸡蛋,说是今天开始过年了。这就是人生第一个关于过年的记忆。这第一个年印象最深的,是大人们都突然不干活了,一个个笑逐颜开,见面以后喜气洋洋,打骂嬉笑,甚是热闹。还有的就是大人们都开始闹着喝酒。男人们个个酩酊大醉。隔壁的陈叔叔醉酒后,在床上爬起来,立在床头前闭着眼睛撒尿,不小心身子一歪,头碰到床沿,跌出了一个血窟窿。这一幕把我吓坏了,节后好长时间,我见了成年男子,都往父母身后躲,怕的是醉酒的男人。
以后渐渐大了,所在的子弟小学因文革冲击停了课,父亲就把我送回农村老家上学。我的老家处于郑州和洛阳之间的黄土高坡。在那里,家家户户都住着土窑洞,记得那窑洞门前是随处可见的土质悬崖峭壁,无遮无拦的甚是吓人。由于历史上所处六朝古都文化圈的缘故,那里的民风淳朴,乡民重孝尚德,村村落落都供奉着佛爷关公。乡亲们的一些语言和礼节都遗留着淡淡的古韵风情。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在奶奶身边过了几个童年的春节。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老家的春节,礼节重于物资的享有。重头戏是从年三十晚上开始的,天一擦黑,家家户户就开始包饺子。那时因为贫穷,包的饺子,除了少量的几个是白面的外,大部分是黑乎乎红薯面的,由于红薯面发糟,皮就擀的很厚,吃起来完全没有白面皮的爽口。包完饺子,先把几个白面饺子,供奉在老佛爷前,(等年过完时,这几个白面饺子就成了我的特供)。再先孩子后老人一人一碗黑饺子。吃完了,大人们会给孩子们分一把花生瓜子,然后开始就着煤油灯守夜。孩子们是熬夜不长的,忍困不住就会睡去,有时憋尿醒了,看见大人们还在虔诚地守着灶神说话。天快亮时,大人们就会督促孩子们起床,穿戴完毕新衣后,自家孩子就会一起摸黑出门,顺着悬崖峭壁边的小路,爬坡下岭去长辈亲戚家拜年。我和几个孩子来到一家家亲戚门前,先高声大伯二婶三奶奶的喊,待开了门后,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就是一个响头。开门的长辈们假装生气,笑眯眯的骂道,“小龟孙,天没亮就来讨食,能饿死你呀!”骂完,就端出一簸箕搅和在一起的花生瓜子红枣,一人一把塞在口袋里。等亲戚家转完了,各个口袋也满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过春节,很少听到人们放炮竹,这也许是当时物资匮乏的缘故吧。过节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新衣服,吃饺子,和给长辈们拜年的礼数。
等到进入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到了城里,男孩子们也长到了淘气的年龄。到那时,过春节才渐渐听到了年炮声。但那时的炮声不是点燃的鞭炮。而是类似现在压制在铝箔上药丸一样,印制在红纸上的火药豆。那个时代男孩子们动手能力都很强,一个个找来人力车车条,折成手枪状,枪的两头,一头是车条帽,帽得小槽正好装进药豆,另一头是与车条帽合槽的车条,正好充当撞针。装填一次,爆响一下。此响虽然单调,但孩子们是成群的,于是乎,炮声此起彼伏,声声不断,孩童们玩的不亦乐乎,倒也给春节增色不少。但是,这炮仗玩是好玩,但也忒危险,那火药燃点太低,稍加摩擦或碰撞,就会爆燃或爆炸。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玩伴在漫无目标的淘气,其中一个叫李明的动作过大,只见一股黄烟从其身上冒出,他妈妈给他新做的黄色上衣前胸,立即变成白花花一片,他忙去用手拍,结果拍一下掉一块,拍一下掉一块。开始他在玩伴面前还装硬,嘴里说“没事没事”。但说着说着就撑不住了,蹲在地上嗷嗷地哭了起来。
进入到七十年代中旬,流着鼻涕四处乱窜的孩童,已变成自命不凡的风流少年。每到春节,就会按耐不住青春的寂寞,开始给妈妈套近乎,试探着让妈妈准备几个菜,请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坐坐。那时的物质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稍有宽裕的父母们爱子有加,就开始了接纳。于是,一人破例,引来了连锁反应。中学的同学们一到春节,就会轮着坐庄,那几天,个个骑着自行车,一群群一家家的乱窜,天天酒足饭饱,煞是神气。
在个人踏入社会前的阶段,因为有父母罩着,且由于思想单纯,性情浪漫,每年春节都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些天,日常生活处处都显示出轻松美妙的情趣。没有压力,没有烦恼,风流倜傥,对未来充满幻想。
进入到七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步过渡到青年阶段,这期间由于青春期和物质的变化。春节期间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渐渐多了起来。
1978年,我踏入了军营,开始了军旅生涯。在部队,因为我所在岗位享有飞行员的伙食待遇,所以与过去家中相比,生活上就是天天过年。其过年的伙食质量则更是无以伦比。也就是这时候,在当时国民还在实行粮食定量供给的阶段,我已经对巧克力、茅台酒、鱿鱼海参等,有了亲密接触。在部队,过春节比较简单,其主题是会餐、逛街、看电影,而请假逛街则是重中之重。那时年轻人正是英气勃发的阶段,一天到晚在军营里闷得发骚,所以,一到假日,满街上都是三三两两结伙闲逛的军人。至于逛街的目的,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转眼间,在部队服役了三年,耐不住对家乡的依恋,我拒绝了长春民航对我的聘请和部队提干的可能,在1981年春节前夕,向部队提出了复员申请。申请递出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班里的两个女兵悄悄对我说,“下午到我们寝室去一下。”接到邀请,我显得很忐忑。因为,这两个女兵是典型的东北姑娘,泼辣好爽,性情外露,平时在班里有点什么事,就叽叽喳喳,毫不掩饰。今天的邀请我自觉有点反常。为慎重起见,我拉着协理员一起到了她们宿舍。
宿舍里除了她俩,还有其它班里的两个女兵。和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特意摆着苹果、瓜子和水果糖。我坐下后,她们就天南海北的聊,我和协理员也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聊了一会,只见她们相互使了个眼色,突然都不说话了。少顷,我们唤着小李子的涨红脸地对我说:“班长!我们真的不想让你走!”她说完,其它女兵也七嘴八舌的对我说着挽留的话。于是,我明白了她们的用意。说实话,递了申请后,我的心情也很纠结,毕竟是呆了三年的军营呀,当过兵的人,哪一个不懂得部队和战友情谊的分量!但对这几个女孩子的真情挽留,则大出我的意外。此时此刻,也算油嘴滑舌的我,竟然一时语塞,好长时间没有言语……
沉默间,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起哄声,原来,在我们谈话间,其它连队的几个调皮鬼,竟然在窗外盯着我们,偷听着我们的谈话,也许是戏看够了,就发出了起哄声。
我和协理员回连里的路上,协理员半开玩笑地责备我让他当了电灯泡,尔后,也很认真地说,“听说提干指标很快就下来了,你等一等不行吗?”我轻轻地叹了口气,不平的思绪又飞回到了家乡。
我清楚记得,离开部队那天,是在春节前夕。送行的大巴前围满了部队首长和战友。千叮咛,万嘱咐!真情切切,令人动容。我和班里战友强忍泪水,一一拥抱。告别中,我却没有看到那几个女兵战友,纳闷间,觉得非常缺憾。车启动了,我身子探出窗外,向战友们挥手,忽然,泪眼朦胧中,我看到了她们,她俩手挽手远远地站在人群外的林荫大道旁。我急忙向她俩挥手,可是,她俩一动不动,只是静静地带着艾怨的眼神看着我,那身影,像是照片的定格,更像一尊雕塑。我只好也默默地看着她们,看了很远很远,直到营房在眼前消失……
复员后好多年的春节里,我的心头时常会浮现出这尊雕塑,久久地无法抹去……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应该是最美好的年代。社会安定,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改善,人们追求理想和进步,信心满满地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憧憬。在这个阶段,每年的春节,也是最丰富多彩的。记得那些年的春节,放烟花爆竹、和朋友们喝酒和看春节联欢晚会是三大主题。那时放炮竹,就是可着劲的放,放的是欢愉的心情,和后来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放炮竹的复杂心情完全不一样。而喝酒则是痛痛快快地喝,不醉不休。不知多少次喝的踉踉跄跄夜半而归,被老婆拒之门外,只好蹲在墙角披星戴月跟耗子作伴。可乐的是,有时夜醉而归,敲门敲得比较响,住平房的几家邻居娘们,都以为是自己的老公回来了,所以,不同房间都传来了骂声,“喝不死你,到狗窝里去睡吧!”而看晚会则是开心地笑,整个晚会都会守在电视机旁。要说那春节最温馨的,还是喝完小酒后,和童年的女儿背靠床头,依偎在被窝里,一边天南海北地说着故事,一边乐呵呵看电视的感觉。那种天伦,是我后来多少年都品味的温馨记忆。
进入到九十年代后期,人们过春节,就多了些复杂的因素。那些年,几代人原有的奋斗理想和美好憧憬,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昨日还在单位里为党国豪情万丈尽力尽责的人们,一夜间,被忽悠的找不到了北,尔后又像难民一样被无情地驱赶街头,生死无人问津。于是乎,往后的春节里,几多家庭少了欢声笑语,多了些唉声叹气!尽管爆竹还在放,可迸发的不再是全家的快乐,而是想惊动苍天,希冀神灵的保佑!尽管酒还在喝,可那是浇愁的酒,是让廉价的酒精麻痹自己,希望在醉里梦里能寻求一下往昔的欢愉!只是那春节联欢晚会,还是和以前一样红火。满目金碧辉煌,一派莺歌燕舞,先歌颂领导英明伟大,后鼓吹百姓幸福乐业,间或拿些街头小民耍耍活宝。等折腾够了,再依依不舍地难忘今宵,信誓旦旦地明年会更好。但不管晚会怎么折腾,我和很多人一样,不再理会那片儿和谐天地,而是小酒喝罢,带着一年的身心疲惫,早早地孤身睡去,梦里去寻求自己的黄粱去了。
2000年以后,我的春节记忆,大多是在春运的道路上。
那年的一个春节里,我闭门苦思冥想,终于下定决心,到南方谋生。春节刚过,半百之年的我,伴着漫天大雪踏上了南下之路,那凄凉的心境刻骨铭心。此后,每年春节前,如何回家,却是过年最大的主题。面对汹涌澎湃的返乡大军。我混在年轻人的队伍里,像揉面团一样被拥挤着推搡着。等回到家里,已是只有喘气的劲头了。多少次,面对进门的我,老伴就会一声感叹,“我的老农民工终于回来了!”
记得那年,我在南方安顿之后,老伴带着女儿过来小住。临近春节,我杭州朋友费尽周折为我们买了火车票。结果一家人在车站裹来揉去,硬是手拿车票上不了车。看看实在是上车无望,我只好带领一家人坐上高价黑大巴,北上绕道,千里曲线才平安到家。在家中稍喘口气,打开随身行李,骤然发现,准备向亲友们显摆一下的许多金华火腿,包装在,腿没了。
就是这样,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近年的春节。
……
2014年的春节就要来了,已经开始思归的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起了曾经意气风发信心满满,与我同时代的骄子们,特别是想起曾经一起成长和奋斗的孩娃、同学、战友和同事们,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往昔春节里的笑声和泪花。我并不祝愿他们发大财,再去追求神马伟大的理想。只是祝福他们阖家安康,因为在当今社会世事叵测,道德沦丧的环境中,平安地活着是重要的事。
回望2013,我的2014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欢快不足,忧郁有余的节日。但我认为老伴说得好,“有没有挣到钱不重要,只是人平安回家就好!”
当前政治家们都爱讲复兴之梦,未来的梦也设计的很好。但我认为,梦没有变为现实之前,眼前重要的是抓紧寻觅上路的车票,旅途中看好口袋里那一点点保命的银子,别让那些无所不在的花言巧语的骗子们再掏了去。
我更希望春节里我也做个好梦,这个梦就是:政治家们伟大的复兴之梦实现了!我和苦难的一代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春节了!
写于2013年12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