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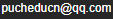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写《围城》的大学问家钱钟书把窗比喻为房屋的眼睛。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关了门也可以生活。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说是天的进出口。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般。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坐享清明。
老作家郭风先生曾出了本散文集,书名就叫《开窗的人》,还援引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的一句话作为题记:“世界被窒息了,打开窗子,让自由的空气吹进来吧。”学贯中西的施蛰存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主编过《现代》杂志,在青年郭风的眼里,这种期刊“也好像是个窗口,使我开始向某一远方眺望一种尚不理解的文学景致”。仅十年文学生涯的诗人徐志摩,曾表示想“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当今的大学生对窗亦有深刻的认识:窗是阳光的眼睛,空气的港口。窗使人的视线得以延伸,眼界为之一阔。它规模虽小,容量却大。门可泊“东吴万里船”,窗更能含“西岭千秋雪”呢!冰心60岁时曾凭窗看雪而思接千载:从唐僧在八百里通天河碰到的“剪玉飞棉”,联想到刘玄德冒雪草堂求贤;从贾宝玉早起揭窗惊呼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联想到毛泽东浩叹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如此的壮怀,皆得益于窗外风物对灵感的激发。
被称作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闭关锁国的年代虽未能走出国门,却能通过心灵的窗户,观察世纪风云,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想。世界因为有人烟而生动,窗户因为有烛光而温馨。写过《恶之花》的波德莱尔一口咬定:“不会有什么东西比烛光照亮的窗户更深刻,更神秘,更丰富,更难以思议和光明无比。”
李商隐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把“君问归期未有期”时的那种情感说得人心欲碎。孟浩然过故人庄“把酒话桑麻”时,还要“开轩面场面”,多么地有情调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句,认为只要有窗户可眺外界,寄寓小屋也挺好。或有窗风吹乱案头的书稿,我们会咒一声“清风不识别字,何故乱翻书”,其实此时的心境是纡徐自在的,不至于是真骂罢。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门属于物质,窗属于精神。常见人贴窗花,挂窗帘,装百叶,摆花盆,甚至做暗号,把窗扉布置得艺术而幽奥。却少有人花诗心在门上,顶多是贴红联以志喜,画门神以抵煞,置猫眼以防贼之类,透露出主人的狡黠与务实。难怪缪塞的诗剧中有妙语说:父亲开门,请进的是物质上的女婿,而女儿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进的。这让人联想到朱丽叶的窗专为罗密欧而开。也有小偷喜欢爬窗的,那绝对与诗意无关,另当别论。窗设在墙上,可称作牖;开在屋顶,则叫天窗。茅盾少时就觉得小小的天窗会使人的想像锐利起来,还说发明天窗的大人是应得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来。眼睛早早被喻为“心灵的窗户”。
孟子云:相人莫良于眸子。通过这个“窗户”,我们拥有了大千,同时也让外界了解自己。房屋的窗户,也像人的眼睛,观察和被观察是双向的。时下一些刊物名曰《世界之窗》、《环球博览》云云,正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而称一些服务机构为“窗口行业”,则是让外人从这些“窗口”读出我们的虔信、文明与高效。
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