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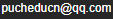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梦想常伴苦涩和磨难,以梦为马,我将奔向远方。我总会笑着对别人谈起途中千疮百孔的现实,像古罗马的角斗士炫耀身上的疤一样,不在意掀开那些陈年旧痂,似乎那是英勇的象征,是和命运搏斗过的馈赠。
但是,
唯独你是例外的,我会羞于对你提起我的伤,因为我的痛你总在感同身受,甚至会把痛苦放大千万倍的加在自己身上,你的存在成了桎梧我自由飞翔的风筝线。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的生命并非独属于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希望我活的更好,笑得更美。你曾为我伤心大哭,为我的欢乐流泪,你像是一棵附生在我身上的藤,因而我天生被赋予了保护你的使命。
1992年,你生育的疼痛在大地蔓延,我诞生于黑夜,倾心于远方,自我出生之日起,你我便聚少离多,远方是我的梦想和搏杀的疆场。也许是身处外地的原因,我越来越感觉到你对我的依赖,越来越频繁的梦到你,梦里面都是你早起为我煮面的样子,低眉垂目的你把全部的心思都注入那一锅面中,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窥视的目光,也许你不曾留意头上潦草扎起的发丝正随着你手上的动作摇晃,想你夜里的叹息声——悲伤又无力。
我忽然记不起你年轻时的摸样,时光雕刻了你的眼角,那段制造在过去的记忆像你煮面时隐藏在氤氲雾气后的脸,模糊的只有轮廓。
时间是永恒存在的,流逝的只是他承载的生命,在时间的流离,你我都无法回头,只能无悲无喜的任由时光在心里冲刷出无法抹去的痕迹。然而对这些日积月累的变化我总是很难察觉,只有当某一日翻看那些泛黄的旧笺时,才会惊出一身冷汗。心疼你的衰弱时你已经老去,数遍你的皱纹时你已经老去。你像那一座生养了我的镇子,爱我的记忆中渐渐陈旧。
你打电话给我时说过你总是梦见我小时候的事情,你说长大后的我惹人厌了,所以才总是没有梦到,我莫明的觉得酸楚。你我相处的时间只有月底。我匆匆的回来,然后再匆匆的跳上开离小镇的客车。终究这样的匆匆没有留下稍许记忆。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匆匆是否值得你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菜色。
离开时客车刚刚发动,你也跳上车告诉我可以再陪我坐一会,我算了一下陪我坐五分钟的车程意味着你要在初冬的白霜中花十五分钟走回去。看你语调轻快地又重复了一遍昨天夜里和今天出门前叮咛的琐事,我悄悄的咽下嘴边的那声拒绝,咽下去却哽在了喉咙。
我的目光越过你,玻璃窗上你我的影像亲密无间的折叠映在一起,正让我想起了蝎子,产下儿女后母蝎子便以自己的血肉作为她的孩子们生命中的第一餐。我就如同那小蝎子正残忍的以另一种方式吞噬着你的血肉使我的影像更加清晰。你把生命中最年轻的部分供养给我成长,毫不吝惜的向我付出这一切,这让我无以回报的一切。我便来自于你,一个正垂垂老去,越发陈旧的你。
我祈求时光可以在这一刻延长,让我多停留在你身旁,也许情非得已,我必将与你远离,但是我的心将永远贴近你。
我,以梦为马,将流浪抹在额头去追寻那远方的月亮,纵使利剑横贯胸膛,我也要挺直脊梁。只要我回首,苍老的你从未稍离,指引给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