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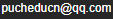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上帝是仁慈的,他没有拒绝我,于是,我回到了十九世纪。在鸟语花香绿树环绕的小山坡旁,以一株葵花的形象静立在那儿等待着我的文森特。
我的周围全是葵花,当然,我也是一株葵花,一株普普通通的葵花,一株在焦急地等待中,面朝太阳的葵花。
流水潺潺,我的心绪也如奔流不息的小溪任意流淌。虽知生命只有一天,然而我愿我这最后的一天,如织绵的天空,更加绚丽;如幽幽的群山,更加深邃;如似火的骄阳,更加灿烂。十二分的急切、十二分的期待,只为等待着我的文森特。
终于,当太阳温暖着我,绿荫又来亲吻着我时,他来到我的面前。带着他的画板和那掩藏不住一身疲倦、一脸忧伤来到了这儿。他发现了我,一丝惊喜划过眉梢。旋即他坐下来,我们面对面。他开始画我。
他是个有着橙色瞳孔的荷兰男人。我心里黯念道。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睛已越来越有神。他手中的画笔不停地挥动着,肆意地在画布上泼洒出我的神韵。时而停下,凝视着我......
我们彼此望着对方,他的眼睛吞噬了我,我觉得我的身体在慢慢地消失,消失在他欣喜的眼神里,也许他已经从我的身上找到他艺术的灵感。可他却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个女孩――一个只剩下最后一天生命的女孩从遥远的未来来到这里,甘愿变化成一株葵花,就在他的面前,就在他的画中慢慢成形。
风起了,凉丝丝的,似乎在提醒我:该告别了。几星花瓣也悄悄地离开了我的身躯,飘啊飘啊,如金黄的蝴蝶,翩翩飞舞着,别离在小溪里,小溪热情地张开双手簇拥着它们,叮叮咚咚向远方流去。我望着随水而去的花瓣一动也没动,他也仍然埋头与他的画作中。我们面对面,他画我。我看他。
我多想轻轻呼唤他的名字,去安慰他那只受伤的耳朵。可是我不能,因为我只是一株葵花,仅此而已。
好了!终于画好了!他轻轻地说。
我听着他那激动无比的声音,看见他迅速地收好画夹,带着那复杂的笑容转身离开,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还来不及分享他的喜悦。但他的话音像融进了风里,轻拂在我的耳边;他的笑容又如五彩的云霞,萦绕在我的身边。
上帝来了,我知道,我该走了。上帝带走了我的灵魂,也带走了我对生命的渴望。
告别生命,才知道人世还有如此多的牵挂。一天,我俯瞰人间,看到一群穿黑色衣服的人来到了一场葬礼上。葬礼上只有寥落的几个人,隐隐地能听到一点哭泣声。在简陋的棺木旁,我看清了死去的人的面孔。那是多么陌生却又多么熟悉的一张面孔啊――我亲爱的文森特。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渴望着生命却甘愿成为他笔下的一颗永恒的葵花。而他拥有生命,却因世事的无奈而放弃了生命,永远地合上了他那可以吞没我的双眼。我的灵魂感觉到了一阵阵的疼痛,我隐约地感到我的梦幻、我的追求、我的希冀也许将和我的文森特一起永埋地底。
然而,若干年后,当以我为原型的向日葵的文森特作品备受后人推崇时,我的灵魂不再哭泣,我的文森特也不再寂寞。逝者已逝,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永恒。
我微笑着,看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