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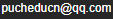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之一。它讲述了一个坐享祖业的男子岛村在旅行中与艺妓驹子和一向处于圣洁状态的女孩叶子的故事。两个女孩,一现实,一虚幻;一热烈似火,一清冷似冰;一如夏花绚烂,一如秋叶静美。她们性格设定的明显差异,以及一男两女的情节模式,很容易让人想到张爱玲的名作《红玫瑰与白玫瑰》。
驹子在与岛村的关系中,一向是居于主动地位的。或许从一开始,当岛村以谈话者的姿态进入的时候,她内心就已经情愫暗生了。他们的相见只能一年一次。于是驹子相当珍惜见面的机会。她陪宴也好,醉酒也罢,都不忘几乎每一天去见岛村,哪怕为了躲着人得从偏僻的山路行走、得藏进壁炉里,哪怕她嘴里总说大概没时间过来,哪怕每次只能匆匆来又匆匆别过。她是爱岛村的,即使明白这样的爱无法改变他的过客身份。这样激烈的感情与娇蕊类似。在张爱玲笔下,这是一位可爱的、妖冶的、声名不好的甚至有些放荡的女人。她出场时是王太太,有富裕的老公,和安逸的生活。但在跟振保相处的日子里,或者是由性生爱,或者是日久生情,她竟然爱上了他。她跟老公摊牌,说要离婚,即使最后没能跟振保在一齐,也结束了这段婚姻;她在振保晕睡时在他病床前哭,在他醒来时默默走掉。某种好处上,这次她用了真心。就如她最后成了朱太太抱着自己的儿子在电车上跟振保相遇的时候说的,他教会了她很多原以为生命里不存在的东西。
这两个女人都对自己的爱人有期盼而无要求,爱得直接纯粹。但这样的感情是有前提的。对于驹子来说,且不说行男是不是她为了救助而甘为艺妓的未婚夫,行男的行将就木之驱和最后的死亡使得她完全能够自由地爱岛村,能够几乎无顾忌地表达。而娇蕊与振保的爱更是萌生在娇蕊的丈夫出差去新加坡的这段男性空缺的时期。这期间的娇蕊是相对自由的。而且,她有夫之妇的身份为振保带给了足够强大的安全感和说服自己跟她偷情的重要理由。这几乎能够说是这场红玫瑰之恋发生的先决条件。很难说振保是否爱上了娇蕊,但是这至少是让他难以忘怀的一个女人。而岛村大概是喜欢驹子的,因为她的洁净。这是川端康成反复强调的最初的情感动因。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女人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以严寒的雪国和极度难得的绉丝作为象征性的衬托,除了与日本向往冷寂的艺术追求相关外,或许也是为了凸显驹子虽是艺妓却有着不一般的净。
川端康成是借雪国这样一个旅行的时空,展示了一场纯粹的爱恋。而张爱玲是在平常生活的裂缝中,安插了这样的故事。《雪国》有强烈的非现实主义的色彩,岛根的形象很弱。只是在行文间隐约提到,他家境大概不错,在东京有家庭,懂些艺术。如此淡化的男性形象,使人觉得,他的被创作似乎就是为了与驹子的相遇和相爱。作者只但是借了他的眼睛和心,未曾想赋于他太重太多的东西。而振保是普遍好处上的好男人,他的形象很充实。英国留学归来,不错的工作,家里有弟弟有母亲。男性形象的差异性不好生硬比较,但这样的设置使得《雪国》有些类似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游仙题材,是存在于异空间的想象;而《红玫瑰与白玫瑰》便不得不堕入繁重的尘世生活当中,无处超脱,无法自拔。前者的结局是上扬梦幻的,而后者只能肉身沉重。这能够从叶子和烟鹂的形象分析中见出端倪。
叶子在《雪国》中一向是有些虚幻的存在,她若隐若现,却承担了岛村心目中近乎女神的形象和整篇文本中悬念冲突的集中体现。她是谁她是关心她弟弟的姐姐,或者似乎是将行男照顾得无微不至、旁若无人的情人,亦或者还是与驹子不甚交好的情敌。但同时,她柔弱,她有着好听的声线,她痴心,她不是艺妓。她每次都在岛村的视野中飘然而过,愁情满怀,欲语未尽。如果说驹子还是可感有触的女人,那么她只能尽似于仙,或者更确切地说,尤物。不只是岛根对她有很多疑问,读者也是。而这些疑云,随着作者对她向善、向美这两个维度的描绘直接有些失真却又确切地成全了她的神性。这就似乎注定了她不能跟着岛村去东京,她只能逝去,因为有神性的东西总是不能融于世俗的。所以她丧命了,在一场火灾中。对她生命终结的场景的描述显得凄美悲壮,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式,叶子落下来的二楼临时看台上,斜着掉下来两三根架子上的木头,打在叶子的脸上,燃烧起来。叶子紧闭着那双迷人的美丽眼睛,突出下巴颏儿,伸长了脖颈。火光在她那张惨白的脸上摇曳着。而需要注意的是,应对这样的死亡,川端康成用了这样的描述不知为什么,岛根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川端康成有着与文本中岛村相似的经历,且不说在岛村身上有着多少主体投射,川端康成就是借岛村的感觉告诉读者,她并没有死。那她变成什么了呢或者蚕,或者仙,大概是随着神性飞升了吧。她本就是叶子,本就该长存着,就算以飘零的姿态。
而作为振保的妻子在的烟鹂相对于叶子的精彩来说,就显得相当淡漠了。()如果说以叶子作白玫瑰是突出其圣洁的话,那么烟鹂的白就只能是扁平、单调。虽然张爱玲在开篇就说,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但很明显,烟鹂给人的感觉没有圣洁,只有乏味。她是女学生,她最开始的时候有着少女的美,也与婆婆相处融洽,但这样或许由于新鲜产生的正面效应太短暂而很快就消失了。她因生女儿很吃了些苦头而觉得能够发些脾气,婆婆却以为她未能生儿子所以不待见她,于是最后搬离了她与振保的家;而时间长了之后,振保也觉察出她的乏味。她不会与人交际,在家里没有地位,连女佣都能够给她脸色看。她好心表现出与客人的亲近,却常常过分,常常以祥林嫂般的诉苦方式因而引起客人的反感。她在振保的生命里几乎没有存在的位置。或许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义和存在感,她与在振保眼中相当不堪的小裁缝偷情只有在比自己更低的人那里,她大概才会发现自己的价值。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讲,这个女人都不圣洁。凭着张爱玲对世情的洞明,她大概不是想创造一个失败的圣女。她的意旨大概是在写明平常夫妻生活的单调。它就是这么无聊,这么惹人厌烦,而这就是活生生的生活。于是,最后的结局里,坏过一阵子的振保又突然变回了好男人,生活如常。
如果以驹子、骄蕊为红玫瑰,以叶子、烟鹂为白玫瑰的话,似乎能够看到在两个文本中红、白玫瑰的倒置现象。虽然红玫瑰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热烈,但白玫瑰却是不一样的圣洁。在《雪国》中,白玫瑰明显是以高于红玫瑰的地位存在的,虽然在描述中,一向是红玫瑰不待见她、压着她;而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只有红玫瑰才是振保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的浪漫想象,白玫瑰只是他不得不理解的妻现实而已。当然,文本展开空间的不一样完全可能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两位不同国别的作者对两类想象中的女人的别样塑造。相比来说,红玫瑰是川端康成的小说中更现实的女人形象,而白玫瑰是张爱玲文本里最后终结于的现实。红、白玫瑰对两类女人的不同想象,或者说是言说方式,也许有着类似于文学母题的好处,能够照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