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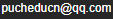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在福州求学期间,每逢寒暑假照例回家。蜗牛般速度的大巴车沿着当时的福厦公路爬过莆田进入惠安,车窗外扑面而来的就是淡淡的海腥味。这时我心里就会对自己说,到家了。
当时家在泉州,父亲在福建医科大学任教。那是在七二年结束到平和山区下放后调回来的。之所以说“回来”,因为这里原来是华侨大学所在地,父亲曾是华大医疗系的教师。在我眼里,数学楼还是那样高,外语楼还是旋得漂亮,但与在当初在华大时,已是物是人非。儿时的玩伴所剩无几,东南亚腔的侨生们也都无影无踪……所幸,海还在。
从小就在厦门岛长大的我,对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关于海的最早记忆,应该是儿时在厦门的“海口”也就是轮渡一带,奶奶带着我去看船来船往;及至后来,每年夏天都会去海里游泳,一泡就是一下午然后仅穿着游泳裤走回家让太阳晒得身上尽是细微的盐粒……
泉州的海在华大一带,是内海。也就是一退潮就出现滩涂那种。滩涂上跳跳鱼很多,但无论如何就是抓不着,记得当年华大男孩子人手一把弹弓的日子里,我们也曾用弹弓打过跳跳鱼,但那仅是为了练习准头,因为即使打着了,小跳跳鱼也已稀烂真是罪过。滩涂上还有许多小蟹,两只前脚一边大一边小大的那个呈鲜艳红色的那种,后来知道学名叫招潮蟹。有时候,这种蟹非常之多,整个海滩上一片红色,随着你走向前,它们会迅速钻进小洞里;你走到哪儿,海滩的红就呈倒扇形地褪色到哪儿,很容易让你想像自己是一艘船……
一涨潮,海水漫过,这些小精灵全部没在水下,看不见了。但海这个时候才显出其广且大。那年从南京乘客车到无锡,车上一来自山西的小女孩大概上初中,随她母亲来江南旅游。车经太湖,她大为兴奋大叫太大了太美了。我在边上告诉她,这不算大,大海更大更美。她转头看着我问你见过大海吗?我说我是厦门人。她眼睛立马亮了说,厦门!我以后就是要读厦门大学,因为那儿有大海。她母亲当然不失时机地对她进行要好好读书之类的教育不在话下。
有时长在海边的人很难想象有那么多人没有亲眼看见过大海,其实这非常正常,就如我去新疆前也没有见过戈壁是什么样。早年间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在海边大排档喝啤酒,接到一北方朋友的电话,听说我在海边,非要我让他听一听潮声,我只好跑下沙滩将手机对着大海……。听到了吗?我问。听到了!电话那边是激动的声音。
厦门是一个岛,当然是四面环海。可在1958年一条花岗岩海堤把厦门变成了半岛。这在当时是个创举,让我有在六岁时坐在爸爸的肩上看到火车直接驶入厦门岛的记忆。但也因此,海水被阻隔,生态严重被破坏。儿时在海边捞小虾捡花螺的日子越来越模糊。前年报上说,由于几座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的开通,海堤的通道作用几近消失,准备要在海堤上开一个六七百米的大口,让海水重新流动进来——可是,为什么不索性全部拆除,还大海一个真实的流畅?或许海堤是一个时代的成就,不能让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吧,但就是这样有限地还大海一段通道,也是我十分期盼的。那天车过厦门大桥,我盯着海堤看,施工正在进行,看来厦门的大海还要继续委屈些时日……
大海与高山比较,大海是沟通高山是阻隔。因而面对大海容易引人遐思。因为世界上只要有海洋的地方无不与你面对的大海有联系而且是实际上相通的,这就让人产生很接近并不远的感觉。由于海之广大,那一边就是世界各地——汉字很聪明,就叫它们海外。海外有同学、朋友,分散在海的那一边,因此,面对大海,我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他们。浪涛轰呜水花飞溅中,真想大声喊一嗓子,你在他乡还好吗,这当然是以前。以现在通讯之发达即时工具之灵巧,海外如在眼前。基本上,每天,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无所不聊,新名词叫——海聊。嗯,还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