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Right ©2010-2024 普车都 jbh.credit189.com/puchedu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用户的投稿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邮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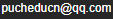 。
。
读赵丽宏的小说《童年河》,让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的《驼背少年》。一样写的是童年,本雅明写的是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赵丽宏写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童年。
同本雅明一样,赵丽宏以一个孩子的视角,用朴素却细腻的文笔,书写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那个年代童年的场景、风物、情绪与氛围。这样的文本,在本雅明时代儿童文学的版图中,都属于不一样的风景,在这天,就更显得写法异样。因为,眼下儿童文学个性是儿童小说,不是故意蹲下身子,乔装打扮成童年,就是高架着身板,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和午后品茶的姿态,回顾品味童年,操着大人的腔调,贩卖大人那一套成长哲学,作传奇或离奇甚至装神弄鬼状的,实在太多。如此矮化和高拔这样两类,几乎成为儿童文学中童年的叙述主调。赵丽宏的这部《童年河》,却以另一样的叙述方式,令人惊叹地抵抗这样目前儿童文学的既定模式,努力使童年得到本真质感的还原。
儿童文学中的主角,一般是儿童,但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孩子背后往往有大人的隐身。《童年河》不是,它的主人公雪弟,就是一个从崇明岛乡下来到上海的孩子,从小说的开始到结束,他始终是一个孩子,并未在小说中跳进跳出。赵丽宏以风格化的书写,完成了对雪弟人物的塑造,也完成了对那一个时代童年的勾勒。
我之所以说这样的书写是风格化的,是因为赵丽宏所选取的书写方式,和本雅明类似,有意避开了外化的情节式的惯性,而采取了内化的散文式的点彩晕染,更注重的是细节和心理。在那里,多年散文创作的经验帮忙了他,成为这部小说别具一格的强项。小说中,初来上海的雪弟,一系列关于景物的描述,无论是河水、芦苇还是声音,在雪弟潜意识中与乡下景物的比较中,真实而巧妙,又极有层次感,完成了雪弟从初闻海关大钟那个陌生的“上海的声音”,到重逢亲婆时“家的声音”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仅是城市与雪弟的相互融合,更是以心理促进小说内在情节发展的动力。这样的书写方式,在当今儿童文学中还是十分别致而值得称道的。
之后,雪弟在家里白墙上画画,养蚂蚁,尿床,探访鬼屋,偷吃苹果,老猫死后为其画像,接到彩彩的来信后爬上房顶,看到母子两只猫如白光在黑暗中融为一体……写得都十分精彩。个性是尿床和苹果两节,朴素至极,细腻感人。亲婆从乡下来到上海,雪弟再不怕尿床了,夜里,亲婆会用尿盆接他尿尿,在嘘嘘把尿的声音中,雪弟闭着眼睛痛痛快快地尿了出来,“水流进尿盆,叮叮咚咚要响好一阵,这声音,有时会把雪弟惊醒,他睁开眼睛,看见了站起面前端着尿盆的亲婆,亲婆总是对着他笑,还会开玩笑说:‘尿这么长,像牛尿。’雪弟也迷迷糊糊地笑着,撒完尿,拉起短裤,扑倒在床上,过几秒钟就又睡着了。”写得如此亲切温馨,是因为那样地吻合孩子的情绪与心理,让孩子会心会意。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这种细节与温馨的把玩或咀嚼之中,而使得小说的格局变窄。小说很好地完成了对那个时代背景的勾勒,同时,又没有将那个时代水发海带一样生发出许多离奇的情节出来,蔓延出小说之外。雪弟刚到上海看到家里哈琼文那张女孩手捧鲜花骑在母亲肩头的招贴画,卖收音机的商店里播放的“社会主义好”的歌曲,以及吃喜鹊、苹果和饼干的心酸,和彩彩的一家被遣送回乡的无奈,还有从大世界跳楼的那个修霓虹灯的工人……如本雅明不动声色地勾勒出1900年前后的柏林的时代一样,赵丽宏细致蕴藉,又恰到好处,很有节制,抒发了从解放初期到反右到饥饿时期以及对上海历史缅怀的那个年代的复杂丰厚的感情。它们不仅仅成为小说的时代语境,也成为了雪弟成长的生活背景,使得这部小说有了宽阔的延展性。
小说也有不足,主要在童年的书写中没有将成人的我们自己完全剔除。这在雪弟初来上海迷路后,雪弟关于有骗子也有善良人各种各样人的感慨;养蚂蚁之后,雪弟关于没有什么比自由更为可贵的收获;在大世界看到顶碗少年的杂技之后,阿爹“做任何事情,要紧的是坚持到底,不要放下”的教导,都有所表现。它们基本上脱离了雪弟自身,是我们大人忍不住跳将出来在自说自话,对于一部纯净的童年小说,多少有些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