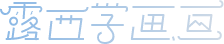傅儒(溥心畲)
简历 生于1896-1963
国籍:中国
年代:近现代
流派:
溥心畲【yu第二声】(1896年9月2日~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
人物生平简介
溥心畲之父载滢为奕訢次子。溥心畲的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澄,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畲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畲出生满5个月蒙赐头品顶戴,4岁习书法,5岁拜见慈禧太后,从容廷对,获夸“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6岁受教,9岁能诗,12岁能文,被誉为皇清神童。溥心畲幼年除于恭王府习文,亦在大内接受“琴棋书画诗酒花美学”培育。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十余年,再迁居颐和园,专事绘画。1924年迁回恭王府的萃锦园居住,涉足于社会之中,开始与张大千等著名画家往来。两年后,他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首次书画展览,因作品丰富、题材广泛而声名大噪,获评“出手惊人,俨然马夏”。1928年应聘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执教,返国后于北平国立艺专沐雨春风,其后又与夫人罗清媛合办画展,再度名震丹青,被公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1932年,溥仪在“满洲国”当了伪皇帝,溥家兄弟趋之若鹜。溥心畲却拒任伪职,并以一篇著名的文章《臣篇》痛斥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继而怒骂这位堂弟“作嫔异门,为鬼他族”。
1924年冬宣统出宫后,溥心畲遂与溥雪斋(号松雪),溥毅斋(号松邻),关松房(号松房),惠孝同(号松溪)等创立了近代著名国画团体松风画会,自号“松巢”[2] 。松风画会是京津画派的主要成员,迄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畲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为贴补家用,
亦曾在自宅开班授徒、至亚洲各国讲学,并以愧对前清先祖为由,拒绝了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拜师习艺邀约。在其自传中,溥心畲提及居台期间,曾为堂弟溥杰夫人回大陆夫妻相聚之事与寻找战后失落的末代皇后婉容之下落,数度赴日;由于溥杰之妻乃日本昭和天皇舅妈之女,故他赴日时曾住居日本皇宫,还与天皇聊聚旧事;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昭和天皇曾问他:“身为亡国的贵族有何感想?”
1959年,台湾历史博物馆特地为他举办个展,展出作品多达三百八十幅。1963年11月溥心畲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年仅68岁,葬于阳明山。1991年溥心畲长子溥孝华病危,家宅遭歹徒入侵并杀害其妻,由于溥孝华早已将其父遗作藏于壁内,致歹徒遍寻无所获;溥孝华去世后,遗物处理小组乃将溥氏遗作一分为三,分别交由文化大学华冈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馆托管。
溥心畲的这些珍宝包括书法175件、绘画292件,以及其他收藏书画13件,砚石、印章、瓷器等58件,总计543件。华冈博物馆托管的为大小画作、各体书法、笔记、注疏及手稿等百馀件;故宫托管的则大作、小品、立轴、长卷俱全,并包括难得的鬼趣图册、西游记册与自绘瓷瓶、磁盤和四小幅自绘漫画,这是溥心畲在国外期间与人沟通的随笔之作。除了台北,吉林省博物馆也拥有不少溥心畲溥心畲的传世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传世墨迹“平复帖”及唐代韩干“照夜白”,据传都曾是溥心畲的旧藏。
溥心畲得传统正脉,受马远、夏圭的影响较深。他在传统山水画法度严谨的基础上灵活变通,创造出新,开创自家风范。溥心畲的清朝皇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使他悟到荣华富贵之后的平淡才是人生至境,因而他在画中营造的空灵超逸的境界令人叹服。《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云,“近三十年中,清室懿亲,以诗画词章有名于时者,莫如溥贝子儒。……清末未尝知名,入民国后乃显。画宗马夏,直逼宋苑,题咏尤美。人品高洁,今之赵子固也。其诗以近体绝句为尤工。”
艺术评价
溥心畲天资颖悟,用功又勤,因此虽然在比常人更多不利因素的压力下,他仍有极高的文采与艺术成就展现。他自许生平大业为治理经学,读书由理学入手及至尔雅、说文、训诂、旁涉诸子百家以至诗文古辞,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视书画为文人馀事。这使他毕生未能将全付创作精力投注于绘画之中,然而这虽是他的不足,却也因此使他的画风露出一种高雅洁静的人文特质,为常人之所不及。
溥心畲的画风并无师承,全由拟悟古人法书名画以及书香诗文蕴育而成,加以他出身皇室,因此大内许多珍藏,自然多有观摹体悟的机会。他曾经收藏一件明代早期佚名画家的山水手卷,细丽雅健,风神俊朗,俱是北宗家法,一种大气清新的感觉满布画面,溥氏的笔法几全由此卷来。因此其所作山水远追宋人刘李马夏,近则取法明四家的唐寅,用笔挺健劲秀,真所谓铁划银钩,将北宗这一路刚劲的笔法──斧劈皴的表现特质阐发无馀,并兼有一种秀丽典雅的风格,再现了古人的画意精神。
观察溥心畲的作品时,在画面上的任何一个部位,无论在表现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种文人心灵、鱼樵耕读与神趣世界的向往,还有远承宋人体察万物生意,与自然亲和的宇宙观及文化观,皆可谓完全谨守传统中国文人精神本位﹝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构﹞,而拒绝了与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之文明结构﹞沟通的可能。然而他的书画作品却并未落于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内涵的真实与精采,只因他的世界本来如此。
从溥氏外在表现的艺术形式上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较新颖不凡的创见。然而艺术的创造性并非仅著眼在外在形式上的考量,赋予旧形式之内涵有新的生命诠释,则有另一层重要的创作意义,却很难由粗略的表面观察所能认知。就这点而言,民国以来的艺术史研究可谓并未给予溥氏应得之评审。
然而在时代的意义上而言,溥心畲亦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